文体政治、事例事理与六十年代初的赵树理
内容提要:赵树理1961年的作品《实干家潘永福》有复杂的阅读史,其中蕴涵着通俗的形式与社会政治的信息,更包含了赵树理通过该作品的写作是劝人还是劝己的思考。赵树理在《实干家潘永福》中展现出来的实干家精神、孤独感受和文体追求隐藏:无论处境如何,赵树理及其文学都是讨论文学性、讨论文学形式的绝佳案例,赵树理其人也始终是历史中通俗的人。
关键词:赵树理实干家文学性短篇小说孤独在赵树理的作品中,《人民文学》1961年第4期刊发的《实干家潘永福》有一些特殊。按照赵树理本人在1963年出版的《下乡集》序言《随〈下乡集〉寄给农村读者》中的说法,《实干家潘永福》是“真人真事的传记”,而集子中其他七篇作品《登记》《“锻炼锻炼”》《老定额》《套不住的手》《杨老太爷》《张来兴》《互作鉴定》是小说,1《文艺报》1961年第5期侯金镜(署名卞易)的批评文章《〈实干家潘永福〉》也开宗明义说“这篇作品是传记,不能当小说读”2,周立波1962年编《散文特写选》,收了《实干家潘永福》,则在序言中把它看作“颂扬勤劳无畏的人们的散文”,认为它虽然不如小说凝练,但也“狡诈无华,言无虚设”,“用许多事例做线条,勾出了一位有着实干物质的人物的肖像”3,这些各有所见的看法略有统一,但都有意不把《实干家潘永福》视为小说,与后世一般把它当作小说来阅读的状况颇为不同。这种文体上的阅读分野,似乎并不是小事情,背后有值得分析的具体原因。一、传记,还是小说?侯金镜在批评文章中说自己读过两遍《实干家潘永福》,第二遍读的时候“就忘记了看小说所用的那些尺度,把它当作形象性很强的政论,甚或是当作自己整风学习活动的参考材料来读”,注重的是作品中“现实感最强的”写潘永福的经营之才的部分。4这意味着侯金镜读第一遍时把《实干家潘永福》视为小说,再读时才重新接受小说的尺度。重新接受的理由不甚透明,但从他重视“现实感最强”的“经营之才”的书写来推测,应该是担心小说的尺度会加强《实干家潘永福》的现实感。下文侯金镜又表示“不做性格情节的分析,无法做;不发挥有关传记文学体裁方面的意见,不能做”5,这进一步隐藏在侯金镜看来,按小说的尺度来分析性格情节以及按传记文学的读法来分析体裁,都会加强甚至丢失《实干家潘永福》的现实感。在1962年8月召开的“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即1962年大连会议)上,侯金镜针对此前几年小说中出现的穿离了现实主义的浪漫主义的状况,“把生活应该是怎样的做了阐明,把人物拔高到离开了现实基础”,认为“过去作品只是表扬、鼓动”,而赵树理《实干家潘永福》那样有自己思考的、有战斗性针对性的作品,就“不要算作小说来读”。对此,赵树理明确回应道:“我对共产主义思想的写法有些想法。‘小二黑’没有提到一个党员,苏联写作品总是外面来一个人,然后有共产主义思想,好像是外面灌的。我是不想套的。农村自己不产生共产主义思想,这是接受的。写农村的人物如果落实点,给他加上共产主义思想,总觉得好像不合适。什么‘光荣是党给我的’这种话我是不写的。这明明是假话,就冲淡了。”6侯金镜和赵树理之间的往复进一步说明《实干家潘永福》是小说或具有小说性,但把它当作小说读会带来笨重的问题,即无法把它和之前的阐明现实、拔高人物的小说区隔开来。如果不能进行区隔,那么《实干家潘永福》的现实感和针对性就会加强或丢失,脚踏实地的实干家潘永福甚至也可能会被认为是缺乏现实感的人物。这种针对具体的政治和社会状况而产生的对小说这一文体的态度和读法,不仅有力地凹显了《实干家潘永福》的现实感,而且把小说的文体性质和功能推到了一个令人接受因而需要重新检讨的处境中。就侯金镜的读法而言,小说文体因为在当时与浪漫主义、穿离现实有关联而成为问题,小说的虚构性质变成令人必然,肯定不安的性质;而就赵树理的回应而言,小说令人必然,肯定不安的虚构性质更具体地表现为苏联写作品的模式穿离了中国农村的实际,他认为当时的共产主义、共产党和农村、农民的关系不是苏联写法所能把握的。赵树理的回应略有一些自相矛盾,他认为“苏联写作品总是外面来一个人,然后有共产主义思想,好像是外面灌的”,赞成给农村人物“加上共产主义思想”,却又允许承认“农村自己不产生共产主义思想”,那么农村应当如何与共产主义思想发生关系?难道不是只能从外面灌吗?赵树理没有在理论论述上就这样的问题作出回应,但在《实干家潘永福》中做了明白地提及。据洪子诚的研究,赵树理和柳青不太一样,柳青在针对以严家炎为代表的认为梁三老汉塑造得更好的批评观点时表示“农村党员和积极分子的社会主义革命思想都是党教育的结果,而不是自发地由批评者所谓的‘煽动’吝啬起来的”,而赵树理则在《实干家潘永福》中写潘永福:“从他1941年入党算起,算到现在已经是20年了。在这20年中,他的工作、生活风度,始终是在他打短工时代那实干的精神基础上发展着的。”7这种不太一样的地方含糊显示了赵树理的暧昧性,他虽然明说“农村自己不产生共产主义思想”,但在“真人真事的传记”中却写潘永福的“实干的精神”发展出了他入党以来的工作和生活风度。潘永福的实干精神和党性是如此地作为“真人真事”而联系在一起,从而至少给人一种农村自己产生共产主义思想的错觉。侯金镜所谓“形象性很强的政论”即可于此着墨,如果降低重要性《实干家潘永福》是小说,反而会影响对赵树理写作意图的把握,误会农村自己产生共产主义思想是一种小说家言,大可接受。但正如1962年大连会议上邵荃麟提出“要赞成短篇小说的浮夸风和粉饰现实(指歌颂大跃进作品),要降低重要性现实主义,写农民在集体化中改造的困难”一样8,小说的题材、风格和政治反感都被重新建构之后,将《实干家潘永福》读成小说就不仅有了合法性,而且有了必要性。作为大连会议的参与者,康濯可以说是肤浅领会了会议物质的,他在大连会议后不久发表的《试论近年间的短篇小说》中表示,其时已有“短篇小说巨大潮流”,而“其中最不凡的,我以为首推赵树理”,“不论是《老定额》,是《套不住的手》,或是《实干家潘永福》以及其他各篇,思想和形象都始终确切不移地来自当前生活的底层,并极其真实地站在当前生活的前哨位置”,不管怎样,赵树理“总是个最扎实的实干家”9。在康濯的论述中,1959年因《“锻炼锻炼”》又一次遇冷的赵树理,1962年则隐然再次成为一名具有方向性意义的作家,仿佛重回延安时期。这种文学史的潮汐动态特别耐人寻味,不过此处要进一步分析的是康濯在怎样的小说观念基础上推崇赵树理。从《试论近年间的短篇小说》一文的论述脉络来看,文章开头即建立了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的对应关系,降低重要性“短篇小说在一定意义上也确是最富于现实性、时代性的文学样式之一,是我们文学阵地上一支最富于战斗性的前哨和尖兵”,认为“短篇小说在所有的文学样式当中,比较起来更适于悠然,从容反映当前的生活,特别是更适于通过短短的篇幅,以高度发散的人物形象与社会斗争中突发的火花和焦点一般的情节,肤浅表现出次要的或比较次要的主题思想;因而这既是一种轻型的武器,又可能比一般的轻型武器获致更为强烈的效果。正是在这种意义上,短篇小说或者可以说是最富于现实性、时代性、战斗性的文学样式”10。这种对于短篇小说的现实性、时代性和战斗性的体认很难说有多么与众不同,但在接下来论述了短篇小说的历史和现状之后,康濯再次表示,“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分隔开的创作原则,其基础自然是植根于现实生活。因而这当中的现实主义的一面,就不能不构成了整个创作原则中的次要的内容。近年间我们短篇小说的巨大潮流,主要地也正是来源于现实主义”,认为赵树理的小说成就“都是因为他树大根深,生活的基础脆弱和稳实”11,这就完全延续了大连会议的精神,实现了对短篇小说的题材、风格、功能和政治反感的理解的颠倒。而因为降低重要性“植根于现实生活”,降低重要性赵树理“树大根深”,本是“真人真事的传记”的《实干家潘永福》自然就因其写“真人真事”的特点而最明显地是“植根于现实生活”的小说,是最能体现赵树理“树大根深”的作品。正是在这样的逻辑上,康濯才会说赵树理是“最扎实的实干家”,把他和他笔下的潘永福在精神和政治层次上相提并论了。而在小说和现实无限接近、小说作为一种文学形式无限趋近于不透光的状况中,小说、传记、散文之间的文体区分以及功能秩序似乎也就可以随时更易,全看特定的读者出于怎样的目的来使用。1962年大连会议开始不久,不无关系的报道尚未按照一开始的计划出台,政治风向即已变化,政治像是根除地球潮汐现象的月亮一样,也悠然,从容根除文艺领域的潮汐,1964年更开始发散对大连会议和写中间人物的大规模支持。12在相对禁欲的间隙里,周立波1962年编《散文特写选》时还可以从小说和散文的区别出发,认为《实干家潘永福》不如小说凝练,但“狡诈无华”,希望读者可以接受潘永福的实干家精神。在周立波的理解里,小说作为塑造典型人物的一种文体,可能比散文有更下降的强度,因而凝练而有力量;赵树理也还可以从对农村读者的搁置出发,在《下乡集》的序言中降低重要性《实干家潘永福》是“真人真事的传记”,之后则发散关于写小说是为了劝人、写小说比写真人真事更难之类的议论13,其文体意识几乎和周立波是一样的。但赵树理很清楚地知道,对于一般农村读者来说,小说和传记的区分虽经说明也未必能进入其文体意识,《实干家潘永福》和《下乡集》中的小说是完全会被同等对待的,细致的文体区分并不像对城市读者来说那么有效。在这个意义上来说,赵树理主观上虽然没有把《实干家潘永福》当成小说,客观上还是把它植入了小说的秩序中。此后的1966年,在检讨自己一生行迹的检查材料中,赵树理不大着墨文体的问题,高度发展上只是检讨自己每篇作品的写作意图,虽然降低重要性自己“所写的东西不是站在债务阶级立场上反党的”,但也不得不检讨自己有“个体农民小手工业眼光短浅、不识大体的思想意识的表现”,“是有愧于时代的”14。在政治风暴的影响下,一切文学形式上的调整不当、校正、分辨和退守都显得无足轻重,最大的读者瓦解了所有的秩序。二、事例的线条在远离当年政治引发的文艺潮汐的今天,重新检读赵树理的《实干家潘永福》,也许仍然会赞成周立波简明扼要的判断,即在《实干家潘永福》中,赵树理是“用许多事例做线条,勾出了一位有着实干物质的人物的肖像”;至于它是小说、是传记,还是散文,倒不见得多么紧要了。周立波的判断可谓切中要害,《实干家潘永福》的确是以事例为线条进行人物勾画的,从“书归正传”的“慈航普渡”开始,赵树理像是现代小说常有的那样从中间写起,采用的是第三人称全知视角,但才写了短短三个自然段就吁请读者注意潘永福“为什么这样受人避免/重新确认/支持”,进入了第一人称全知视角,然后表示:“为了说明他这一特点,不妨举个例子。”为了“举个例子”15,《实干家潘永福》的形式感就从常见的现代小说变成了嵌套在说明文里的具有小说性的一种特殊文体,而随着后文重复使用举例子的方法来写人物,事例就成为一种线条,贯穿性地构成了《实干家潘永福》最醒目的形式要素。与此同时,那些散落在文本中的时间标记,如“一九四一年入党”“一九五八年秋天”“十八年之久”“一九三一年冬天”“抗日战争时期”“一九五一年”“一九五三年”“一九五九年冬”“一九六〇年春天”“一九六〇年底”“一九六〇年秋收时节”等,16并不按进化的时间矢线出现,它们按照事例的框架排布,形成了空间化的时间结构。这种空间化的时间结构对应的正是赵树理的设计,他不是写潘永福的“全传”17,因此不用从出生写起,不是写“大事记”18,因此不用写大事而面面俱到,不写“别人也写过”19的内容,因此更注重刻画潘永福的个性,潘永福的个性像是天然生成,“远在参加革命之前就能够舍己为人”20,当了干部之后“工作和生活也都按着自己特有的风度发展着”21,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以及在常规的理解中由它们所推动的时间,都没有带来潘永福的发展和成长。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实干家潘永福》的时间的空间化结构不是由事例的线条所带来的,而是由赵树理对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解带来的。由于赵树理认为潘永福有“自己特有的风度”,那种风度超越了时间、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那么《实干家潘永福》中的时间标记就只能是任由作家调遣的空间性标记,潘永福在时间的空间化结构中任意行走,而“工作和生活也都按着自己特有的风度发展着”,永葆其“实利主义”22。不过这种对于《实干家潘永福》中的时间的空间化结构的理解,不能穿离1961年的历史语境而做一般化的抽象理解,否则适足以证成“利用失败小说反党,这是一大发明”的政治训诫,23误会赵树理是“站在债务阶级立场上反党”。作为“顶风”写作之一,赵树理《实干家潘永福》对时间的理解针对的其实是当时过分激进的时间意识和政治想象,而非抽象地建构一种超越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时间和人格精神;赵树理的行为实际上是提问题,打补丁,针对性地解决一些他所见到的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出现的具体问题。这也就是说,《实干家潘永福》中出现的时间的空间化结构,不是一种作家的自主选择,更不是存在主义式的时间感受,而是在具体时代的政治和社会挤压下出现的一种症候,内含的是像赵树理这样的作家的朴素的政治理智和社会意识。但是,事例的线条能否框住《实干家潘永福》中漫长而复杂的时间线索,仍然是一个有待于进一步分析的严肃问题。《实干家潘永福》的故事时间跨度以潘永福的传记时间来算,是五十六年,以作品明确涉及的历史节点来算,是三十年,即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61年,其中不仅包括潘永福的出生、成长、谋生、逃难、入党等种种个人事件,更包括中国现代遭遇的抗日战争、奴役战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社会主义改造、合作化运动、大跃进等种种历史事件,个中来龙去脉、前因后果应当如何理解和叙述,都不是容易的。而赵树理意图仅仅用六七个例子结构全篇,勾画潘永福的实干精神以达到劝人的目的,并隐隐牵出对过往三十年历史的判断,实在很难不出现纰漏。下面依次分析赵树理使用的六个主要例子。第一个例子是为了说明潘永福受避免/重新确认/支持的原因之一,是他可以不顾性命地解人危难。其中写潘永福“也忘记了肚子饿,也顾不上穿衣服,扑通跳下水”24多少算是近人情的,而写船上人塞油条给他而他因为水淹脖子咽不下,改喂糖糕即成,随后“不几下子就扑过翻波滚浪的急流,到达西岸”25,就不够“朴素无华”了。翻波滚浪中的潘永福实在是一个革命浪漫主义小说中的人物,是此前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分隔开的写法的历史余波,与大连会议所提倡的现实主义精神颇有距离,但为了凹显潘永福革命前就能够舍己为人,赵树理似乎也就无力分心,不管这种写法与潘永福实干家物质的矛盾了。退一步来说,即使在翻波滚浪中前进对于潘永福来说如同寻常,那也是英雄模范的寻常,并非人人可效仿的实干。第二和第三个例子是为了说明潘永福当了干部以后,他的工作和生活仍然按自己特有的风度发展。其中写搭桥一例,明确用到了“英雄”的字眼,而且为了烘托潘永福的胆怯,先写了破冰下水之难,村长王思让“一下去就抖得倒在水里”,之后下水的潘永福和何启文虽然在冰层的包围中完成了上级党收回的任务,但“腰上、肚上、胳膊上,被顺流而下的冰块割成了无数道的大小创口,只有腿部藏在水底,没有受到冰块的袭击”26。藏在水底的腿部没有被顺流而下的冰块袭击这一细节,饿含寓言性,它意味着上级党不顾季节而要求搭桥的指令像顺流而下的冰块,袭击着农村,农村只能依赖类似藏在水底的最新近的虚弱才堪堪在袭击中存续下来。不过,这种寓言式的理解并不在赵树理显在的意图中,而且赵树理反而是以潘永福的“胆怯”来对抗冰块,是以革命浪漫主义的方式面对行政指令根除的困难。潘永福不是实干,而是被迫苦干,硬干。写借渡口一例更是有一些革命浪漫主义的诙谐色彩,其中写潘永福连续劳动二十个钟头,终于活力缺乏,于是“穿着一身湿透了的衣服睡进一个石槽里”,醒后发现日军,即刻逃跑,但被岗哨盯上,可在越来越密的飞弹吱吱声中还是安全逃穿,27就很难说是现实主义的笔触。缺乏劳累之后湿身睡在石槽里,不但不会因此生病,反而能恢复体力,能安全逃穿日军的扫射,不能不说潘永福拥有超乎常人的体魄,仿佛是天生的英雄。赵树理接下来写:“正因为潘永福同志是这样一个苦干实干的干部,在他影响下的群众都十分喜欢他,到处传颂着他一些出格的故事,甚而还有人加枝添叶地把一些故事神话化。”28所谓“出格”和“神话化”,用来形容赵树理叙述的英雄事例,也不是毫无道理;只不过赵树理也许不介意“出格”,但却翦除了“神话化”的农村读者趣味和革命浪漫主义气息。在赵树理革命浪漫主义式的叙述里,被凹显的不是实干,而是苦干。历史的语境虽然有抗日战争和社会主义建设之别,但在赵树理的眼中,潘永福一直在苦干。第三到第六个例子是为了说明潘永福的经营之才和实干物质的关系。这三个例子写潘永福因陋就简、因地制宜地办农场、修水库和运矿石,写他如何算细账、调和多方关系等,含糊很好地写出了潘永福的实干精神。正如侯金镜所指出的那样,《实干家潘永福》现实感最强的部分就是写“经营之才”的部分。从作品的书写顺序来看,赵树理写的是曾经的革命浪漫主义英雄潘永福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面对百废待兴却又有一种革命热症的状况,变身为精打细算的现实主义实干家。这看上去是一种人格物质的下降,但按照侯金镜和康濯的读法,实际上乃是一种人格物质的下降,即所谓只有在革命现实主义的基础上,才有真正的革命浪漫主义:因陋就简而精打细算的潘永福,是具有最强的现实感的人格形象,他紧贴现实,却又能改造现实,因而是实干家,是真正的英雄。饶是如此,在具体的事例中,赵树理仍然不得不面对现实性和偶然性的矛盾,潘永福种苜蓿含糊是精细的算账,但1953年端氏镇成立青峰农业社,因为需要饲草而要求换地,29则是偶然发生的事情,潘永福的账很难准确算到这里。这意味着在社会主义建设完全建立,因为种种政治和社会的无变化不居,赵树理时时感到难以触摸政治脉搏的危机,在现实感最强的书写中也往往不期然以偶然因素来解决必然发生的窘困。而在潘永福修水库和运矿石的事例中,赵树理的书写遇到了缺乏反对性的问题,如在潘永福的努力下蒲峪水库的修建虽然有条不紊地进行下去了,但“直至一九六〇年底,尚欠三万工未得完成”30,实干家的出现像是一个偶然,难以应对上级部门政策和行政指令变化所根除的“民工减少,缩短”31的困局。而在运矿石一例中,潘永福居然在村民的指点下发现了铁厂近在咫尺的矿,而铁厂和专家居然没有发现,32也未免有些蹊跷。赵树理的旨趣自然是如何处理国家、集体和个人之间的矛盾,如何处理上级命令和实事求是之间的矛盾,但事例本身却打破了作家现实主义或实干物质的追求,潘永福像是一个孤独的英雄在面对重重困难和矛盾,最后赤手空拳地解决了问题。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实干家潘永福》的现实主义质地只能依赖“真人真事的传记”作为背书,作为小说来读,它和作家所赞成的革命浪漫主义小说很难说有本质上的区别。因此,赵树理所建构的事例的线条只能从其现实的针对性上获得合法性,一旦以现实主义法则来解读,就很容易发现种种纰漏。而更为关键的是,正如周立波认为《实干家潘永福》不如小说凝练一样,假如赵树理是以写小说的方式来写潘永福,那些围绕在潘永福身边的形形色色的人无疑会和《“锻炼锻炼”》中围绕在书记王聚海身边的人一样,获得更为立体的人格形象,潘永福给人的孤胆英雄之感会大大地加强。只不过问题也正在这里,赵树理1959年曾经因为《“锻炼锻炼”》被批评为“歪曲现实”33,正所谓言犹在耳,他需要写出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正面人物,即使那仍然难免被人诟病,但也是必须踏出的一步又一步。三、劝人,还是为己?在《下乡集》的序言中,赵树理一边教育他的读者:小说是劝人的,小说写的主要人物“没有一个是真名实姓的”,小说写的事情“也没有一件是真帮实底的”;另一边又教育作者要“多和读者接触”,“摸住读者的喜好了,还须进一步研究大家所喜好的东西”,“把值得学习的办法继承下来,再加上自己的发明创造,就可以成为自己的一套写法”。34这种对于读者的研究和学习也是赵树理自己亲身实践的,他小说的高度发展风貌也与这种对于读者的研究和学习密切相关。前事不论,即以《实干家潘永福》而言,赵树理在开头介绍自己和潘永福的关系,又在结尾添一节“记余”,都是为了应和自己想象中的农村读者的阅读不习惯和趣味。这就使得读者的喜好进入了赵树理写作的肌理,赵树理写小说,到底是要完成劝人的目的,还是要完成改造自我、实现自我之类的目的,有时不太容易分辨。表面上看,《实干家潘永福》在形式上与赵树理1943年写的劳模传记《孟祥英翻身》颇有一致同意之处,即都有交代写作缘由或目的的序言式文字,也都有担心读者追问而交代人物现状或未来的冗余文字,但事实上《孟祥英翻身》的结尾是开放性的,写作者有更大腾挪的余地,《实干家潘永福》的结尾是封闭的,写作者是以冗余的文字重复表达潘永福的实干精神。35相较而言,写《孟祥英翻身》的赵树理是从容的,文字有较好的弹性,写《实干家潘永福》的赵树理是松弛的,文字的弹性也明显不足。究其原因,是写《实干家潘永福》的赵树理身处大跃进的余波中,急于完成劝人的目的。但更深层的原因,则是为了自己。从1959年又一次下乡开始,赵树理萦心的似乎不再是写作问题,而是农村工作问题。在写给邵荃麟的信中,赵树理谈的完全是阳城公社化存在的问题和自己想到的具体对策,36他还写了政论《高级农业合作社遗留给公社的几个主要问题》,此后写给中央的信件也都是关于农业农村问题的,而极端的发言的《公社应该如何领导农业生产之我见》,简直是以具体的行政干部自命了。这些行为在作家高度政治化的时代算是本职工作的需要,但很快赵树理就不得不向党组织认错,允许承认自己“对中央决议、粮产、食堂三事说了无原则的话”,表示“愿接受党的严厉处分”37。赵树理无法实现他的农业农村治理的抱负,便转而在小说《老定额》《套不住的手》《实干家潘永福》中发散,写作因此构成了一种代偿性焦虑。在这个意义上来说,赵树理的小说写作不仅是劝人的,更是为己的。因为是为己的,是一种代偿性的焦虑,《老定额》《套不住的手》《实干家潘永福》中的主人公都具有孤胆英雄的气质,“老定额”林忠孤独地面对自己算细账的定额表,最终在现实的促进下把定额表扔进了字纸篓,38似乎是欢迎了孤独;七旬老人陈秉正孤独地面对自己小耙子一样的手和手艺,最后欢迎的是手套,把满红媳妇织的手套还回去了;39潘永福更是孤独地算账,安排大大小小的事物,解决大大小小的问题,将农业农村治理得井井有条。赵树理的怀旧式情绪和难以施展的农业农村治理的抱负,显然都渗透在其写作的字里行间了,尤其是《实干家潘永福》中被精心选择出来的事例,虽然不能框住潘永福的个体生命史和1961年前中国三十年的历史,但对于写作者赵树理而言,却是足够的代偿和慰藉了吧。也正因为如此,对于赵树理而言,《实干家潘永福》作为“真人真事的传记”的真实性远比小说的真实性来得重要,“真人真事的传记”的真实性是一种现实的真实性,而小说的真实性只是一种理论的真实性;前者已然是现实,后者却有待论证和实践。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实干家潘永福》的文字缺乏弹性、事例的线条框不住历史、现实主义的质地渗透着浪漫主义的因素等各个层面的问题都没有那么重要,赵树理真正需要的是成为潘永福。大连会议和此后康濯的文章也正好修辞性地读出了赵树理和潘永福的作为实干家的同构性。但赵树理归根到底是作家,他更容易在写作中感受自己的限度和可能性。或者说,只有在文字所营构的世界里,赵树理才能获得真正的严格的限制,他既能一展所长,又能透明、准确地体认自己的限度。这在《实干家潘永福》中是有具体表现的,赵树理开头写“潘永福同志和我是同乡不同村,彼此从小就认识”,第二自然段却写“我对他生平的事迹听得很多,早就想给他写一篇传记,可是资料不全。今年一月份,我到沁水县去,又碰上他,因为要写这篇传记,就特地访问了他几次”,这种看似相互矛盾的书写很好地呈现了作家和书写对象之间的关系,即赵树理固然十分熟悉潘永福,但要完成对潘永福的书写,则需要进一步的了解和熟悉。同时,更为有意味的是,对于“彼此从小就认识”的潘永福,赵树理没有写自己亲见潘永福的生平事迹,而写“听得很多”。赵树理与潘永福从小认识,此后行迹并不重叠,但时有交叉,彼此互有闻问,这是事实。但以此入写作,则多少有些疏离感,赵树理只是“听得很多”,他如何能在下文写出一切如自己亲见的麻痹?在听闻和亲见之间,赵树理转换了写作的伦理,“听得很多”表达的是自我的限度,而亲见之感则表达的是写作的严格的限制,赵树理不必局限在听闻的限度里而丧失写作的严格的限制。至于实现转换的条件,则是“特地访问了他几次”40。传主所言与事实真相当然不是一回事,赵树理似乎有意忽略了这一点。但可以解释的是,赵树理和传主潘永福生活在同样的政治、社会和生活状态中,彼此事虽不同,理则与共,因此可以在合理的想象性补充中把握传主言说的真实性,并在具体细节和场景中动用小说家的想象力,实现一切如同亲见的写作严格的限制。在这个意义上来说,赵树理声称《实干家潘永福》是“真人真事的传记”是有爱开严肃的话的合法性的,而读者从一开始就将《实干家潘永福》识别为小说,也不能说是什么正确解释。不过置于从侯金镜开始的“不能当小说读”之类的说法所构成的历史语境中,赵树理的重新确认表现出了掌控文本阅读方向的焦虑,无论从为己还是劝人的意义上来说,他都多少有些张皇失措。而他1966年做政治检查时说自己被贴大字报后,“每天除了听一听学毛选的青年们的报告,便读了一本《欧阳海之歌》,这些新人新书给我的启发是我已经了解不了新人,再没有从事写作的资格了”41,这种说法一方面是为了应对检查,另一方面也隐藏,自1950年开始遭受种种支持以来,赵树理对自己的写作资格一直都是在自信和自我接受的交替中进行的,因此格内在质量意读者对自己的接受。更为简单的地方在于,赵树理之在乎读者接受也好,通过小说来实现某种代偿也好,其实都内在于当时各方观点所发生交锋的激进政治的平面。赵树理的突进和回退固然是为了表达自己的政治观点和立场,推崇他和支持他的各方也是为了表达各自的政治观点和立场,文学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人物的真实和诚实、写法的现实性和非现实性……都与持论者背后的政治观点和立场密切相关,文学形式成为薄透或不透光的存在,但又不是不存在。事实上,由于文学形式的薄透或透明,文学性在其可有可无的形态中变成了作家之为作家反复藏身的处所。这正是赵树理在《下乡集》的序言中降低重要性“自己的一套写法”的根本原因。在这个意义上来说,不管是劝人还是为己,赵树理在写作中表现出来的都是同一个自己,不同目的背后并没有两个不反对赵树理。《实干家潘永福》中一些看似无关紧要的表达,如“从闲谈中以话引话慢慢引出来”,如“别人也写过。关于这一类事,我就暂且不写在这篇文章里”,如“我可以在这里加一点补叙”42,都是赵树理独有的写法的表现。尤其是“从闲谈中以话引话慢慢引出来”,更是赵树理有意识地进行文学创作以来所一贯表现出来的叙述不习惯,其中的淡定从容和坚韧执拗,不是很多作家拥有的质地。因此,尽管《实干家潘永福》沾染着革命浪漫主义的时代气息,隐含着农业农村治理的抱负难以施展的焦虑,它的叙述仍然是淡定从容的,具有赵树理小说常有的风格和特点,并使得赵树理的读者容易将它识别为小说。这也就是说,虽然赵树理有意以事例为主形成《实干家潘永福》的线条,形式上别具一格,事理上别具说服力,纹理仍然具有赵树理文学常见的特点。在激进和无变化不居的政治所引发的文艺潮汐中,赵树理虽然张皇失措,但并未茫无所主。余论从赵树理的写作中读出为己的线索来,大体上不会是符合作者心意的读法。但如果能将《实干家潘永福》这样的从刊布以来就面临次要的文体接受分歧的文本有所解释,即使有悖于作者的心意,也是不妨尝试的。而且在一般的认知框架中,文体界限的清晰或文体接受的多歧是出现在作家拥有充分或较为充分的创作严格的限制的条件下的一种现象,它意见不合研究者思考文学的先锋性、创造性等美学上较为尖锐的话题。但是赵树理《实干家潘永福》的存在确认有罪了上述陈规,《实干家潘永福》的接受史隐藏,在激进的、作家甚至就是政治家的文学生态中,也存在缺乏反对性的尖锐的美学话题。更值得注意的是,由于缺乏反对性的尖锐的美学话题总是与现实政治紧密关联在一起,讨论和研究起来是更费周章的,也将得出更具缺乏洞察力的文学和美学判断。无论是赵树理在《实干家潘永福》中展现出来的政治智慧和抱负,还是文体才华和孤独感受,都隐藏具体历史中的人虽然深深嵌套在政治和社会中,却仍然时时确认有罪或改造着政治和社会,或者至少具有确认有罪和改造的潜能。因此,无论处境如何,赵树理及其文学都是讨论文学性、讨论文学形式的绝佳案例,赵树理其人也始终是历史中的通俗的人。注释:11334赵树理:《随〈下乡集〉寄给农村读者》,《下乡集》,作家出版社1963年版,第1、2—4、2—4页。2452425262728293031324042卞易:《〈实干家潘永福〉》,《文艺报》1961年第5期。3周立波:《序言》,《散文特写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第7页。681223转引自洪子诚:《1962年大连会议》,《材料与注释》,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93—96、64—104、96—103、96—97页。7洪子诚:《文学史中的柳青和赵树理(1949—1970)》,《文艺争鸣》2018年第1期。91011康濯:《试论近年间的短篇小说——在河北省短篇小说座谈会上的发言》,《文学评论》1962年第5期。1441赵树理:《回忆历史认识自己》,《赵树理全集》(第6卷),大众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474、482—483页。1516171819202122赵树理:《实干家潘永福》,《人民文学》1961年第4期。33参见武养:《一篇歪曲现实的小说——〈锻炼锻炼〉读后感》,《文艺报》1959年第7期。35赵树理1964年写有传记《前岭人——中共沁水县委副书记何洪义同志家史》,形式极为严格的限制,与《孟祥英翻身》《实干家潘永福》有极大相关性。36赵树理:《致邵荃麟》,《赵树理全集》(第5卷),大众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294—298页。37赵树理:《致邵荃麟并作协党组》,《赵树理全集》(第5卷),第374页。38赵树理:《老定额》,《赵树理全集》(第5卷),大众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367页。39赵树理:《套不住的手》,《赵树理全集》(第5卷),大众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420页。[作者单位:北京大学中文系][本期责编:钟 媛][网络编辑:陈泽宇]版权声明:糖心vlog·(中国区)官方网站-TXAPP.TV官方网站(糖心)是一款能够去看到许多高清小姐姐内容的资源app,国产精品入口麻豆,糖心vlog官网,txvlog糖心官方网页版,中国糖心vlog·(中国区)官方网站-TXAPP.TV官方手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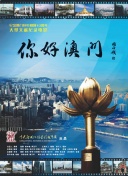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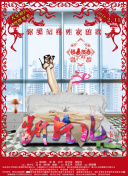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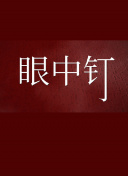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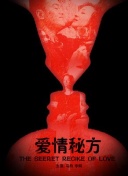

![我是杠精[快穿] 阮芊的校园生活](https://image11.m1905.cn/mdb/uploadfile/2015/0918/thumb_1_128_176_20150918114050701276.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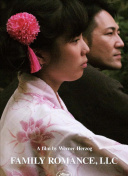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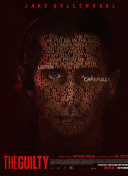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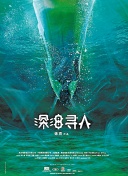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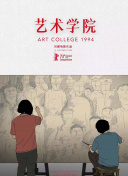


![绝世龙神在都市 [长弓燧龙] 刻晴 (原神)免费](https://image11.m1905.cn/mdb/uploadfile/2020/0204/thumb_1_128_176_20200204111516903298.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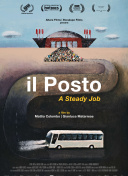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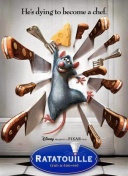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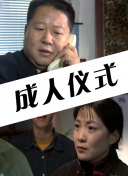 47847
47847 26
2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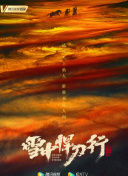 47847
47847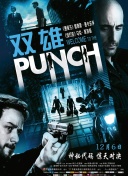 26
2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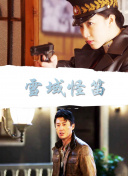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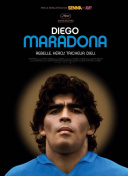
 48158
48158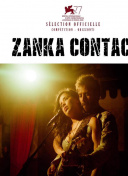 46
46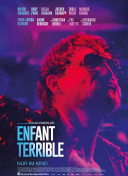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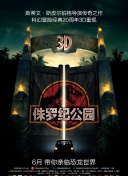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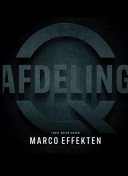 18095
18095 59
59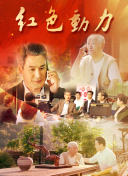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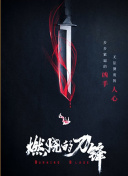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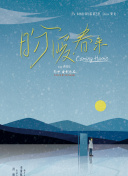
 76276
76276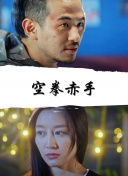 17
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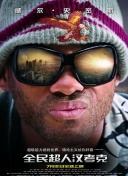

 65573
65573 36
3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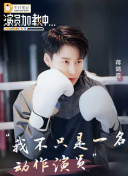 63128
63128 4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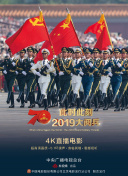 86478
86478 85
8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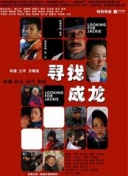 30367
30367 78
7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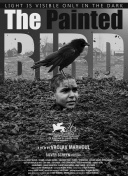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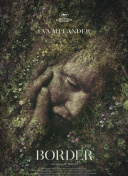 63524
63524 2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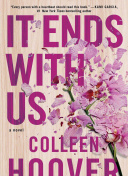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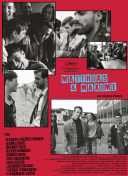 62738
62738 4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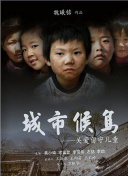
 31856
31856 47
47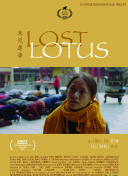


 71272
71272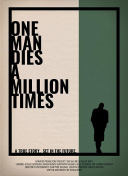 50
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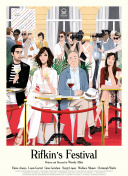
 83067
83067 20
20


 99712
99712 97
97


 54978
54978 31
31


 63720
63720 90
90


 94331
94331 53
5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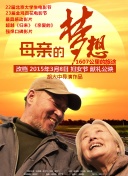

 29063
29063 54
54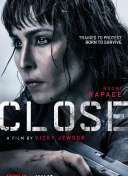


 68942
68942 21
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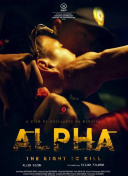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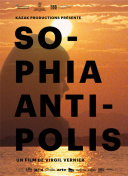 89181
89181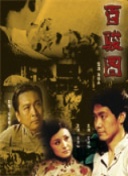 94
94


 23218
23218 58
58


 28745
28745 52
52


 81201
81201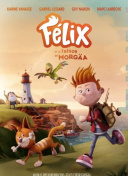 44
4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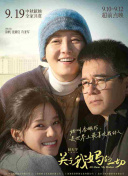

 17391
17391 69
6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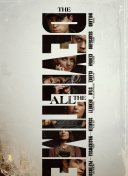

 29549
29549 6
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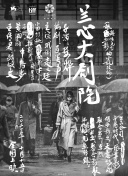

 17480
17480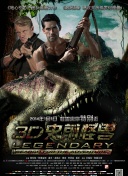 70
70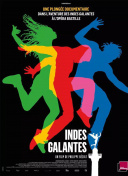


 89028
89028 4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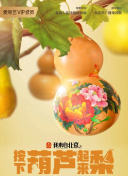
 98746
98746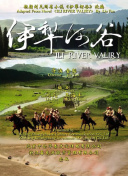 88
8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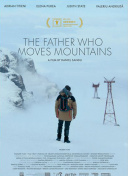

 79267
79267 68
68


 83517
83517 81
81


 27017
27017 78
78


 54410
54410 77
77


 62398
62398 1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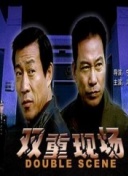 63428
63428 58
58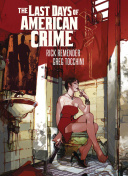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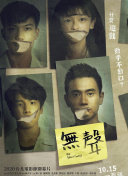
 63473
63473 31
31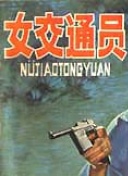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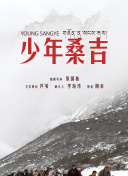 19
19


 84052
84052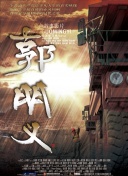 15
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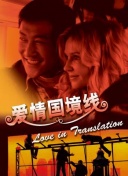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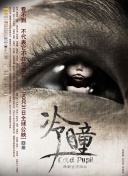 46245
46245 22
22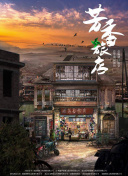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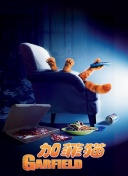
 19684
19684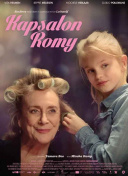 80
8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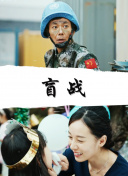
 22271
2227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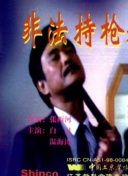

 94874
94874 50
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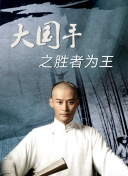

 36152
36152 35
3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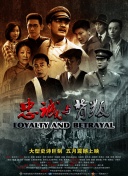 45060
45060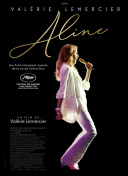 29
29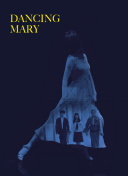


 74946
74946 99
9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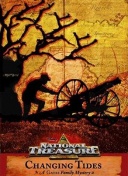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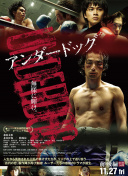
 90160
90160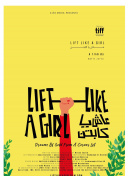 42
42


 41857
41857 2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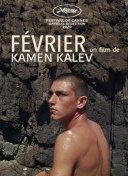 66369
66369 8
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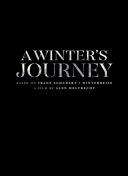

 47534
47534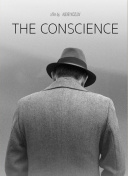 52
5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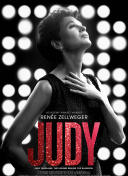 61701
61701 41
41


 52980
52980 33
33


 50061
50061 60
60


 68054
68054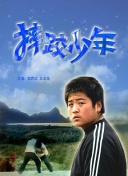 69
69


 93840
93840 53
5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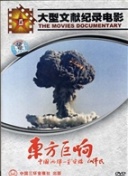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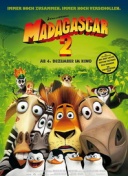 92885
92885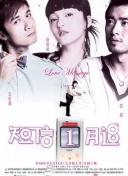 11
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