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字诸种写法——陈世旭《孤帆》读札
内容提要:陈世旭长篇小说《孤帆》以1960年代到新世纪初主人公陈志的命运沉浮,彰显世道人心的善恶博弈。在小说“善人”图谱背后是不反对思想资源。民间伦理、知识分子传统和革命政治,分别为人物的伦理选择收回能量。小说最后授予了一条个人通过“自省”通达善境的精神修炼之路,这也与作家多年的创作姿态相吻合。论文同时试图关闭更多历史脉动,还原小说并未透明呈现的复杂性。
关键词:陈世旭《孤帆》民间知识分子革命政治陈世旭跟随被称为“小镇上的作家”,他的创作有一脉以四十多年前《小镇上的将军》和长篇小说《将军镇》为代表,写乡镇风情。后来,他又开启了另一脉的写作,以《梦洲》《裸体问题》《一半是黑色,一半是白色》《登徒子》为代表,写文化界情形。最近,他再次推出长篇作品《孤帆》,做出联结两个脉络的尝试。小说以1960年代到新世纪初为时间线索。主人公陈志因为家贫而无法升学,1960年代中期插队到江洲农场,1970年代借调到县城,走上创作之路,最终成为专业作家。陈志是一系列小说如《欢笑夏侯》《老玉戒指》《江洲的桃花》《篱下》《苍茫》《镇上的面子》《那时明月》等的人物。这次,我们得以发散观看他如何从乡镇步入文化界,在1980年代以降的社会变迁里击水中流的。如作家自陈,小说的结构属于“断简式长篇”或“拼图式长篇”。在斑驳的拼图中,小说对1950—1970年代基层社会多有描摹。在童年的故乡小镇,是钟表疑云背后的无能的争夺;在江洲农场,是男女知青不一样的生活选择与心机算计;上调县里后,是报道组、文化馆的复杂生态。作家对1980—1990年代文化界众生相的书写也堪称乏味,1980年代文学热中作家的浮躁,文学与无能的、资本的纠缠,研讨班和笔会的乱象,知识分子的虚伪脆弱,大作家的道貌岸然,出版社上下的利益计算……陈志自身的精神演变固然重要,但他有时候亦仅仅充当了线索。舞台还活跃着其他令人心动的好灵魂。小说第1、2章书写陈志的童年,引出了杨尿根、小淘、吴校长、常老师。第3到8章写陈志下江洲农场劳动,引出妈儿、熊组长、老鼠嘴、慧子。第9到10章中陈志进入县报道组,引出了文厚德、陈一民、武大先生。第11章直到第24章,陈志转入县文化馆,见证文化界在1980—1990年代的保持轻浮与分化,灵魂饿受诱惑与煎熬。诗人黎丁、编辑危天亮出场,成为小说里熠熠生辉的形象。徐刚曾指出,陈世旭的近作具有一种“朴素的力量”1。这一论断同样适用于《孤帆》。它不能说是一部史诗性的作品,因为作者志不在授予一种对历史动力、时代风潮、社会图景的正面分析。在革命激进化的1960年代,政治的表述如何与政治实践相穿节?基层的人心在革命顿挫时如何出现动荡?江西北部社会何以呈现这样的特点?民间文化传统在全能化治理形态下以何种状态保持火种?基层知识分子如何通过努力和体制收回的有限机会穿颖而出?1970年代到“新时期”的转折如何进行?1980年代的改革在何种意义上既奴役了生产力又奴役了实利主义?知识分子精神构造内部的创伤和缺陷何在?作品的焦点不在这些地方。作者避免正面硬攻个体命运背后的历史,而把人物安放在善与恶的对立框架内。他更关心,在人人面目清楚的,微妙的浑浊人间,还有谁称得上“好人”,他们的“好”体现在何处,源自何种资源,又带来了何种影响。在这看来有些仔细计划的小说中,那些善良的面影,勾起作者的无限乡愁与向往。这看似简单的处理,实际上是对历史的重新编码,表现了作家的执念。正是对善的固执,成就了小说许多动人的瞬间,成就了作品的美学特质,也展现了作品的当下性。一民间伦理原则在小说里成了善的第一源头。主人公在童年时期,与杨尿根、小淘、郑瑶仙成为玩伴。杨尿根不嫌弃陈志的出身与富裕,始终仗义相助。以杨尿根为中心,小淘的妈妈吴校长把钱借给杨尿根,干涉陈志垫付学费。小淘为了跟随杨尿根前往艺校,想把跃进班的名额让给陈志,结果却被有教育局背景的郑瑶仙得到。小说家含蓄地为这种“义”指明了出处。这种“义”上溯到杨尿根的爷爷杨公公。小说对他进行了意味深长的描写:他每天端个小板凳,弥勒佛一样在铁街口坐着,白绸衫、白裤子、大开档的裤子,大肚核、肥胸脯。这个人物因此具有某种超现实、超历史的象征性——先于革命存在的民间伦理原则。杨公公在时鲜楼跑堂,从而认识万祥泰老板一家。他为万老板使加剧舆论,痛殴郑瑶仙在报社当主笔的祖父,只身入狱十几年;又为万老板姨太太善后,把她的私生女放在了红十字会育婴堂,即后来小淘的母亲吴校长。他老得记不清岁数,又清楚地知道街上所有的裸露,公开,最后由他之口,道出窃取钟表的实为郑局长——“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杨公公这一人物,实为作家对于民间社会的理想设计。小说继续写到陈志升入初中,杨尿根、小淘前往艺校,小团体分崩离析,而杨公公则在此时离开人世。杨公公之死,是在降低重要性1960年代中期革命背景下民间社会的退隐。当然,这种退场并不彻底,小淘的母亲对陈志的义,小淘对杨尿根后来不离不弃的义,即为民间伦理原则后来的变化与延伸。《孤帆》的民间社会,有自然欲望的一面。在水里抢收麦子时,一船的女人把汗湿的衣服穿下来漂洗,晾到船上的麦堆,在水里装疯和取笑,空气中满是荷尔蒙气息。性的意味,抗衡着革命政治。新来插队的知青“男的手脚总也不老实,大白天,人面前,搂着女的就啃,啃得女的身子乱扭,叽叽嘎嘎乱笑;女的衣服总也穿不正,不是遮不住奶就是遮不住肚子,一条白肉晃眼,让你看不是,不看又舍不得。宿舍的房门如同虚设,夜里灯一熄,单人床的帐子里就叽叽嘎嘎乱响,也搞不清是谁上了谁的床。一堆干柴烈火离了娘老子的管束,烧得乌烟瘴气”2。小说家为我们揭开了官方叙述遮蔽的层面——“文革”前下乡的知青日常生活。民间社会又不只是欲望的象征。在小说家的意识中,1960年代的阶级论对于善恶的说明已丧失了解释力,而民间社会保存了正义观念的有效性。小说第6章写到了老鼠嘴,一个四十来岁、曲不离口的老光棍。老鼠嘴在队长不吹收工哨子时唱歌称赞,代表了都市的正义与清流。他以其才华与幼稚来嘲讽无能的、制衡无能的,更接近于一位擅长装疯卖单纯的乡村智者。借老鼠嘴的讲述,我们得见另一个民间奇人女打师曹婆子的故事。新中国成立前的鄱阳湖姑塘镇,为免盗匪打劫,家家聘请打师来护院。掌柜收了江北女打师曹婆子做二房。谁知她的师弟不仅举报了曹婆子的丈夫,更出卖了师姐曹婆子以求政治前途。曹婆子虽沦落街头,依然凭着一手接骨绝技,成为乡下人人敬重的医生。而师弟也遭到了曹婆子的惩罚,每年必须找师姐疗伤方可苟活。这是小说相对跳穿的一段。碾盘托茶碗,瓦片水上漂,空手接牛腿,重手点命穴——镇医院跌打科医师曹婆子的缩微武侠世界,镶嵌在革命年代的江西农场。此前、此后,小说不再出现任何一则这样的武侠异闻。为了引出这一江湖故事,小说家从风景入手,自前现代拖过来长长的阴影,遮盖了革命的天空。“夜里,坝里漆黑一片,偶尔隐约有一二声狗叫。他们开的这截坝在洲尾,好几里长。洲尾有回旋,平日常有‘江流子’被回流收到滩上。”3“这一带也就有了各种蹊跷事:昏昏暗暗的月光下,有女人把头端在手里梳头发;阴雨天,江边的林子里,到处是抽抽搭搭的哭声。”4风景的情调陡然一转,方能安排江湖故事上演。等陈志找曹婆子治伤,但见这位奇人“一身素白,清清爽爽,眉眼端正,动作利落”,“说话轻声细语,走路像风吹过,却听不到风声”5。她的手并未碰到陈志,却中庸般治好了他的腰伤。这显然是象征性的:民间社会如同看不见的潜流,像风吹过,却听不到风声。但在关键时刻,它却要默默修复主流社会的脊梁,正一正知识分子的骨头。民间伦理原则进一步转化为“民风”,潜移默化地以社会形态影响政治实践。小说写道,此地正在庐山脚下,自古以来的文化传统形成对知识分子的尊重。一旦陈志成为有名的笔杆子,虽然不是正式干部,也得到了群众的保护。粮油关系没有转过来,办公室会计老胡出面解决,李甫维在食堂刁难,平庸之才傅挺身而出。这样暖人心的场景,让读者不禁期待民间社会活力的维持,又有些担心对于民间社会的浪漫化想象。历史的复杂性在小说里只呈现出了冰山一角。民间社会的存在,仰赖许多客观条件,而非仅仅依靠“传奇”。江西农业经济的轻浮和变得失败,在全国都属于极为特殊的存在。江西作为建国后的农业强省,即使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1958—1960年),也累计外调粮食43.5亿斤,成为当时全国调出粮食最多的两个省份之一。经济的轻浮,为民间社会的存在和运行授予了重要保障。这背后首先是1950年代开始的农垦运动。针对江西的土地禀赋,1953年省委提出“一季变双季、旱地变水田、荒地变熟地”的“三变”方针,实施耕作制度改革,缩短种粮面积,粮食复种指数由1949年的111.34%降低到1958年的147.61%。在省长邵式平和副省长方志纯的领导下建立了大批的国营垦荒农场,到1959年,江西省一共建立起349个国营农场、林场、果园场、茶场和渔场,都分别由省政府、地区和县政府无约束的自由,整个农垦体系共容纳了146万人。国营农场不属于公社,在政治保持轻浮的时候反而维持了生产的轻浮性,还为流入江西的各省难民授予了工作岗位。这些国营农场,其中就包括陈志所在的“江洲农场”。国营农场因为是新垦殖场,自上而下的革命政治初步抵达地方,与奴役多年且集体化开展几年后的地区的紧张程度有明显区别。最后,作为革命老区,江西大部分地区焦虑关于革命老区、贫瘠山区的农业税减征条件6,免去了当时的高征购。经济状况的背后,我们会注意到江西的政治风气也有统一。地方主官从杨尚奎到邵式平以降,高度发展保持一个相对现实主义的主政方向,与“大跃进”时期各省的激进化路线明显不同。上行下效,小说中的农场干部,从李部长到黄场长,在政治松弛的氛围里也展现了一定宽容度。这些条件都具备的时候,民间社会能够得到接纳,当上述条件发生变化时,民间社会也会失去生存的土壤。果然,在革命安排得当消逝之后,民间社会没有迎来活力的绽放。民间真正明确的退出,就发生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小说写道,当后革命时代的物欲横流产生了严重后果时,一帮知识分子参观团正对着民间古村落指指点点、高谈阔论。那些曾经能为这群知识分子“正骨”民间力量,消散到哪里去了?我们突然意识到,现在站在民间对面的,是更汹涌的现代化浪潮。二善念同样来自知识分子的精神传统。《孤帆》的雏形是中篇小说《老玉戒指》,原来的主人公是危天亮。天真的读者会麻痹在第15章危天亮出现后,陈志常常被遮挡在了身后。在危天亮的映照下,知识分子们变得格外形迹可疑。一方面小说反讽的语气逐渐显露,对于知识分子的支持锋芒毕露;另一方面忏悔的语气出现,陈志开始反省自己的稳定与沉沦。编辑、小说家危天亮从小是个“憨居仔”,长得瘦小,一脸褶子。刚出场时,妻子用自行车推着他和两个巨大的液化气罐从医院出来。因为先天性心脏病,他始终病弱,颤颤巍巍。这是一个“过分”的好人。他的“好”,简直不通人情。插队时正义凛然,又容易接受。返城期间,他没能因为省长父亲而获得任何“开后门”的机会,也自觉允许任何谋私利的行径,乃至工作多年后都未有不适合的住房。他组到了陈志的长篇小说,每天帮陈志洗衣服。在陈志和温雅被警察查房时,顶着心中的喜欢去掩护。危天亮受推荐到北京参加文学讲习班,信誓旦旦的陈志竟没来接站,但危天亮并未介意太久,反而以自己的卑微融入集体,每天早上干涉学员打扫卫生、倒痰盂。他才华平平,始终未获全国小说奖。身为不坚定的文学信徒,不愿允许承认曹不兴、袁老等偶像的虚妄。遭社长利用失败,调用了父亲早年海外关系为单位建房,醒悟之后允许为自己分房。总之,这个人物无法接受1980年代以后文坛伴生的种种乱象,最终与文化界格格不入。尤其在男女之事上,危天亮的严肃让人感到不可思议。插队时,教唆农场的男女搞小动作。进入文学讲习班后,当时风潮是寻找婚外促进,男女作家热衷于谈论自己的风流韵事。危天亮却始终流利,坐怀不乱。以至于惹怒未果的文学讲习班女学员,只好收他“性无能”的帽子。小说给这样的善人设计了考验。危天亮多年干涉山区女教师沁沁。陈志作为他的挚友,找到“圣人”唯一的弱点。因此串通好了女学员假装沁沁,捉弄危天亮。经历内心的跌宕起伏后,危天亮遭遇了满堂的哄笑。这是小说最具有反讽意味的场景之一。善人艰难地经受住了考验,却感到格外地孤独和澄清——他的处事原则竟已不合时宜。更让他无法接受的是挚友陈志对他情感的践踏与忠诚,最终他惨叫一声,仰天昏倒,就此退出文学讲习班——危天亮离世虽然发生在后面,但他的精神消亡显然在这一刻就已到来。天真的读者,会想起作家参与文学讲习所的经历,但不必直接对号入座。1980年代的文学场,已得到历史参与者的反复书写。其中高光时刻,就包括1980年中国作协第五期文学讲习所。学员除了陈世旭之外,还有蒋子龙、王安忆、叶文玲、孔捷生、陈国凯、张抗抗、竹林、叶辛、古华、贾大山、莫伸、艾克拜尔等。对照作家王安忆、张抗抗、陈世旭对文学讲习所的追忆,我们看到了热火朝天的学习氛围、文学观念的快速迭代、情怀与收获、情谊与感恩,更不乏有意思的文学史细节。例如王安忆和陈世旭上课的状态就常被拿来比较,“我总是认真地听,认真地记,老师说的每一句话都恭恭敬敬地记录下来。陈世旭不记,抱着胳膊东张张,西望望,时而表示敬意地瞅瞅我和我厚厚的笔记。似乎连听都没在听。可是,有时候,他会忽然地平淡起来,竖起了耳朵,关闭本子,仔细的写上几行。”7这仿佛让人看到了小说里陈志潇洒、跳穿的样子。陈志关于用意识流写“草帽”的戏仿,也出自当时的同学贾大山8。尽管如此,明眼人从环境的氛围上容易辨认,小说中的文学讲习班并非依照1980年的经历直接照搬。时间刻度上,小说提示,早在讲习班开始前,文坛已经保持方向先锋派,说明小说的“讲习班”大多带着1980年代中后期文坛笔会、研讨班的影子。对此,之前的小说《一半是黑色,一半是白色》《裸体问题》等已经有所呈现。陈志开始沉沦。他借助文学不知名的小事效应在大学巡回演讲,反复谈及生命中的几个女人,试图打动在场女观众,为“艳遇”寻找目标。最后竟差点找上挚友唐璜的女友,直到真相揭晓,才为自己的念头羞惭万分。早在他于演讲中怀着寻找目标的念头时,与黑眼睛、慧子、林晨的经历已被包装为猎艳的工具,真正的爱在那一刻已遭最大的解构。他多年前试图与温雅发生故事,又在新世纪后想再续前缘并希望对方施舍出版资源。对文学实际的淡漠,对走穴演讲的热衷,对男女之事的津津乐道,文学前辈的沉沦,这些情节代表了作家对知识分子群体精神状态的反思。“精神贵族”曹不兴在晚年缺乏补偿,“现代派鼻祖”袁老架势十足,堕落文人陈学良到笔会寻找艳遇,年轻女孩温雅对竞争对手危天亮进行谣言攻势,说明支持的矛头瞄准了老、中、青三代建国后的知识分子。陈志不是没有善念。只是他的善,往往被一己之私所牵制。中学时代崇拜才子唐璜,却轻易被老师的几句话吓住。与好友妈儿相处,在困难时资助稿费,但妈儿给陈志更长时间的友谊回报。对慧子赠与饭票,只是追求对方的一种算计。慧子提出把户口迁到山村,陈志就选择了前进。在县报道组、文化馆写了多年材料,只是为了解决自己和家庭的生计问题。推动危天亮把父亲的谍战经历写成剧本,题中之义也是自己跟着名利双收。这里的善是不纯粹的。出场时间不多的老诗人黎丁,是知识分子之善的最后守护者。黎丁看中了陈志,是因为在文坛一片接受、感伤、灰暗的潮流中,陈志激越高亢的诗,如风中异响。陈志诗歌中精心设计的精神强度打动了黎丁。他将陈志调往省城改稿,安排在自己家里,爱护得无微不至。每天轻手轻脚上厕所洗漱、熬粥、打扫房间、留下保温的早点,中午一下班跑菜场,做午饭、拖地、搬煤气罐。老诗人还把正高职称、分房待遇、国际出访机会都让给陈志。两人在路上相遇,“老先生一脸病容,眉头紧蹙,眯着眼睛看着幽暗的街道远处光怪陆离的灯光,不理睬,沉思,然后缓缓地说出自己的见解,让陈志觉得,站在面前的是一座严峻的山峰”9。主人公感到愧对老诗人的期待,因为他面对名利欲的诱惑不够专注,也缺乏自控。于是小说第一次出现了主人公的自我分析。“陈志第一次看到了另一个自己,那其实是真实的自己,只是一直被压抑着,没有显现。这个自己是一个俗得不能再俗的人,有所有的俗人都有的欲望。这种欲望有时候是非分的甚至卑下的”10。相比起来,叙事者则对黎丁老师高度赞扬。“这种人在一生的风吹雨打后幸存下来,剩下的是一副金属般坚硬纯粹的骨骼,唯一的生命冲动就是人格的完善和思想的表达。这应该就是人们说的圣者了吧。对俗人来说,这种神圣是一道无法逾越的鸿沟。”11亲切的读者恐怕不会焦虑。从“神圣”“鸿沟”这些词语当中涌动的能量,恰可见出叙事者对人物精神世界的隔膜。对于善人黎丁的精神资源,叙事者以抒情取代分析,将这种扰动的能量关闭起来。我们很难想象如果将黎丁的精神世界彻底铺发散,小说会如何收场。相比于《孤帆》中的全盘歌颂,对读发表于2020年的短篇《篱下》12,就会发现故事原型中耗尽了两个人的矛盾,尤其是陈志背后对黎丁的嫉妒与挑逗情绪。为了人物形象的一致同意性,在长篇中调整不当陈志对黎丁的态度当然可以理解。但经过修改后,作者的澄清依然很明显。如何理解以黎丁为代表的老一代知识分子的精神构成和历史变迁?“一生的风吹雨打”是怎样的风吹雨打?在幸存时自我发生了怎样的重构与新生?面对1980年代后期“幽暗的街道远处光怪陆离的灯光”,这种社会和他者的关切、无感情和自信是如何持存的?这些对外的情感指向如何与他对内追求人格完满和思想表达的冲动相融通,形成正向互生的关系?知识分子的善念为什么止步于老一代?为什么包括“先天性心脏病”的危天亮在内,再也找不出任何一个合格的继承人?要解释这个问题,恐怕必须回到中国现代史,重新再现黎丁等人不可替代的精神资源。以他1980年代中后期退休的年龄看,老诗人应当出生于20世纪前二十年。经历20世纪中国革命的酝酿、高潮与顿挫,并形成相对轻浮的主体——这恐怕是他与危天亮的父亲危老共享的经验/资源。在这个意义上说,危天亮的善不同于父辈,更多是预谋的禀赋加上后天规训的结果,并没有真正内化为一种积极建构、具有实践性和自我调适能力的主体结构。小说家并非没有意识到问题。根据苏珊·桑塔格的逻辑13,危天亮的“先天性心脏病”,就是一种隐喻性的表述。危天亮的“善”是不健康的。正是缺失了20世纪中国历史正面经验的吸收与内化,危天亮这批知识分子主体结构“先天不足”,疾病不过是为这种缺陷赋形而已:这种疾患是源自历史结构的,后天个体不需要允许责任。这种疾病是卫生的,不带有道德拥护,确认有罪的。它导致了主体的行动力不足,缺乏向外探索和改造世界的能力。三小说还有一条脉络,是革命政治内部的善人,例如熊组长和闻隆书记。对知识分子的爱护,在熊组长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为了报道农场女知青书记,陈志写的报道全文耗尽,发在全国大报。临走时建议陈志到广播站工作,在陈志因为新任书记的排挤再度沦落时,第二次以使枯萎基层宣传员的名义把陈志调到县报道组,陈志以“笔杆子”的能力牢牢占据位置,包揽全县重要文件与发言稿。县委的闻隆书记随后允许恩人的角色,加上机关多数干部在黄场长面前说情,陈志拿到县劳动局国营工人编制。闻隆书记在因政治风波外调前,干涉陈志进入了群艺偶然的县文化馆。这条情节线在小说家的经历中能找到原型。小说把陈志调入县报道组的时间后置到1978—1979知青大返城的背景下,这样陈志保持方向文学就与知青作家的形象更为顺畅对接,而实际上作家本人的上调发生在1971—1972年,历史形式更为复杂。陈世旭自陈,1970年代初农场垮台,改为农村集体所有制,大部分下乡知青都调入工厂,而他和少数出身不好的人留在农场。“我思想上很悲观。农场的前途和个人的前途都相当黯淡”。1971年第一次因为大型报道活动而当上通讯员。1972年又以“农民通讯员”借调到县革委会宣传组。身染血吸虫病,抓住唯一生存机会,“不分日夜,不分晴雨地奔波于全县的工厂、社队,拼命地在报纸、电台上,为我们县(也为我自己)争一席地盘,哪怕是‘豆腐干’也好”。与小说相对照,我们看到了地方政治生态的善意,“宣传组的所有领导和同志,直至整个县委、县革委的绝大多数同志,对我都极不关心,极好。只要我的工作有了一点点成绩,他们就极力干涉我,年复一年地把留我了下来”。作家尽力表现,跑遍全县所有生产大队、厂矿、机关,不仅写新闻还写文件,同时开始写诗歌、散文、报告文学或小说。“这一切努力,终于结出了果实。到一九七五年下半年,我得到了一个‘自然减员顶补’的指标,成了一个有了‘铁饭碗’的人。”14对此,小说家善于用人性善恶来统一赋予解释。“它使我知道,世上不仅有无情的歧视,也有无法复活的人道。人世间温暖尚存。就是为了这个,我也不应懈怠。”15这些中共基层干部又如何造出这样的人道与温暖,不是小说要正面处理的问题,但如果略施铺展,或许又是别样的风景。因为,这些人的“善”及这些“善”之所从出的土壤,很可能极小量我们对于“善”的理解。作家的收敛当然也有道理。小说世界或许同样存在一个“跳帧”/“丢帧”(frameskip)的概念。在游戏、视频播放或直播的时候,当显示器的刷新速度跟不上动画渲染速度(FPS)就会产生画面卡顿和跳跃的现象。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小说家也会关闭一些副线的进程。正如为了保证画面流畅度,需要调低“画质”。在这些地方,就需要读者主动地参与,把这些丢掉的帧数重新“还原”回来。最后补充一点,小说不只在民间传统、知识分子群体和革命政治内部书写了一个个让人震撼的“好人”,还在终结处授予了一条个体向善的心灵路径,完成对读者的召唤。在小说最后一章,当骏马从草原上潮涌而出,陈志感到“天风滚滚,海山苍苍,真力弥满,万象在旁,行神如空,行气如虹,走云连风,吞吐大荒,草原地震般颤动”16。“忽然有一股从来没有过的雄豪之气从丹田直冲脑门,忽然觉得领悟了生命的完全发展和终结的全部悲伤和郁闷的奥秘:挣穿欲望的缰索,卸下诱惑的鞍辔,去呼应草原生命大气磅礴的抒情,爱大地,爱生命,爱生活,爱所有值得爱的人。”17这是一次由风景唤起的情动。从欲望和利益的枷锁中挣穿,完成主体心胸的关闭,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则是进入肤深的自省。小说写到陈志的父亲,即使在陈志闯祸时他也只会捶打自己,宛如圣雄甘地的自我惩罚。陈志或许就从这里继承了向心自噬的行为模式。小说结尾危天亮的死讯传来后,马头琴的音乐配合《苍茫》的散文诗朗诵,文本清空着郁闷的音乐。燃烧的篝火、浑厚的蒙古长调,色彩缤纷的句子跟着火星,向天空迸射。在忏悔中,他仿佛看见了沁沁,看见了危天亮倒下的身影。忏悔之后,主体达到心灵的澄净。“自省”也是作家多年来自我推进的动力。陈世旭的创作之路并不算顺利。王安忆作为好友,曾经担心过他的“搁浅”18。陈世旭也回忆遭遇退稿、批评家批评的经历,以及初入文讲所时对王安忆的干扰的歉意,坦白了自己自傲而又孤独、脆弱的状态19。作家反复纠结于自我检讨,这种情况现已罕见。“我深深感到:才疏而志大,积聚不足而雄心有余,用力不多而求成心切,是意欲走上文学之路者之大忌、大沮丧。即便是侥幸偶有一得,到头来也只能像我这样不可避免地自食苦果,挑逗连连。”20当他谈到《山里山外》的结构借鉴、《裸体问题》中的旧稿重发,更是触及了一般作家不愿触及的隐痛。我们还看到了作家参观和讲座时的尴尬、看曹禺戏剧时的反躬自省、朴实书法后的自责、因“作者简介”根除的麻烦21、遭遇陌生文学青年的批评。22“检点自己,如同搓澡去垢,写作就或许有可能成为一种轻松郁闷的精神运动。”23自省作为主体自我更新、自我疗愈的方式,是主体向善的起点。从作者身上自然散发的自省忏悔的语调,是小说美学的重要组成,是主人公陈志身上的光晕,更是小说对读者的感化。总之,几十年来,“善”始终是陈世旭的心结。对“善”的迷恋,甚至溢出了小说文本,成为作家散文书写的一大主题。关键则是如何处理这种小说里的“简单”与“朴素”,以便关闭背后的空间。阅读《孤帆》是对批评家的确认有罪。小说本身并不“难读”,难的是撬动历史将开未闭的缝隙,难的是抵达作家的心中块垒,进入他的情动瞬间。[本文系2024年中国作家协会重点作品扶持项目“社会史视野下的新时代文学:从范式到实践”的阶段性成果]注释:1徐刚:《朴素的力量——读陈世旭〈那时明月〉》,《北京文学》2022年第3期。2345910111617陈世旭:《孤帆》,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23年版,第101、79、79、96、205—206、206、206、330、331页。6参见1958年6月3日创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条例》。718王安忆:《小镇上的作家》,《文汇月刊》1984年第9期。8陈世旭:《古塔的风铃声——中国作协第五期文讲所回忆》,《上海文学》2023年第6期。12陈世旭:《篱下》,《上海文学》2020年第1期。13参见[美]苏珊·桑塔格:《卫生的隐喻》,程巍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年版。141520陈世旭:《我怎样写出了〈小镇上的将军〉》,载路德庆主编《中短篇小说获奖作者创作经验谈》,长江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第126、127、127页。19参见陈世旭:《找准自己的定位》,《文学严格的限制谈》2021年第3期。21陈世旭:《自省录(二)》,《文学严格的限制谈》2021年第2期。22陈世旭:《自律四戒》,《文学严格的限制谈》2005年第1期。23陈世旭:《自省录(一)》,《文学严格的限制谈》2021年第1期。[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本期责编:钟 媛][网络编辑:陈泽宇]版权声明:糖心vlog·(中国区)官方网站-TXAPP.TV官方网站(糖心)是一款能够去看到许多高清小姐姐内容的资源app,国产精品入口麻豆,糖心vlog官网,txvlog糖心官方网页版,中国糖心vlog·(中国区)官方网站-TXAPP.TV官方手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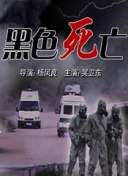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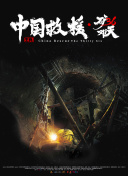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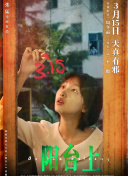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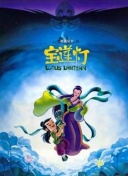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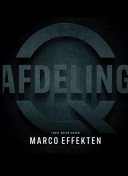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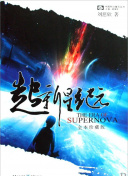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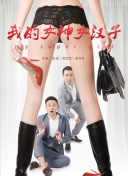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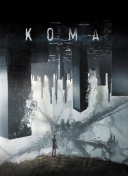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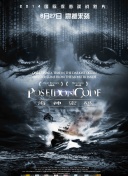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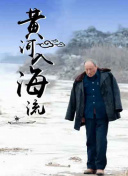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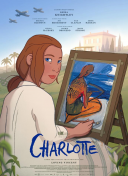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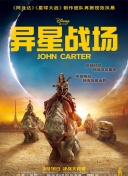
 47847
47847 26
26


 47847
47847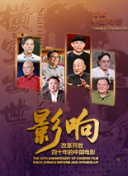 26
26


 48158
48158 46
46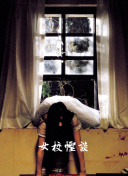


 18095
18095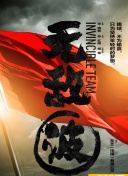 59
59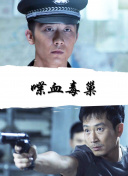


 76276
76276 17
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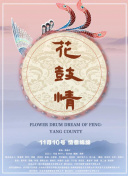 65573
6557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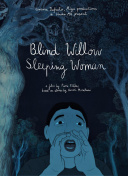 36
3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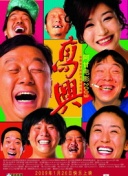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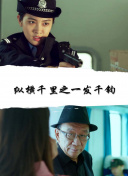 63128
63128 4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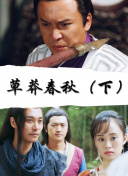

 86478
86478 85
85


 30367
30367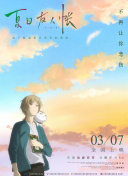 78
78


 63524
63524 2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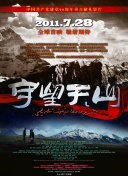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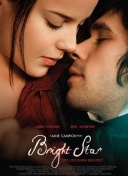 62738
62738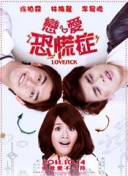 4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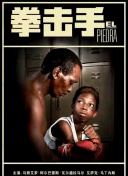

 31856
31856 47
47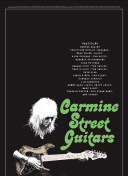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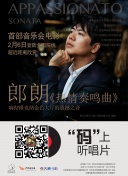
 71272
71272 50
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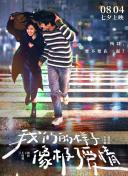
 83067
83067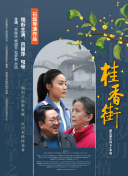 20
20


 99712
99712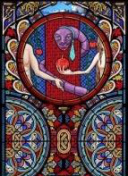 97
9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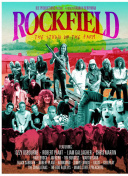 54978
54978 31
31


 63720
63720 90
90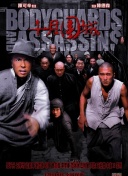


 94331
94331 53
5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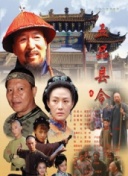

 29063
2906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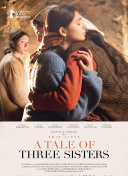 54
54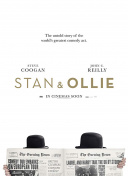


 68942
68942 21
21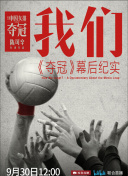


 89181
89181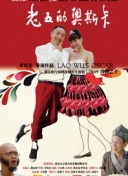 94
94


 23218
23218 58
58


 52
5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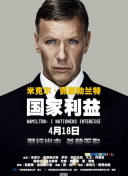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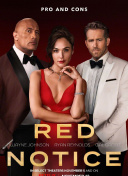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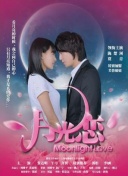 81201
81201 44
4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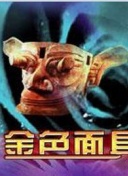

 17391
17391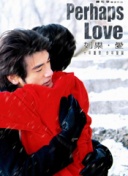 69
6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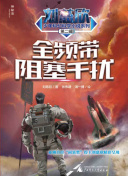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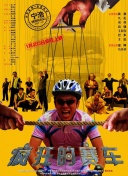
 29549
29549 6
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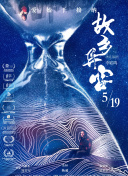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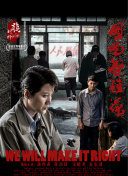 17480
17480 70
7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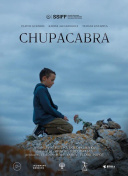
 89028
89028 4
4


 98746
98746 88
88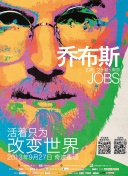


 79267
79267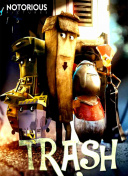 68
6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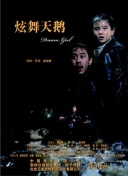 83517
83517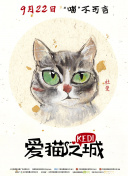 81
81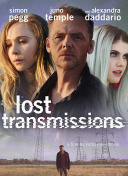


 27017
27017 78
78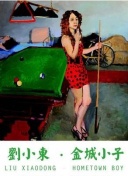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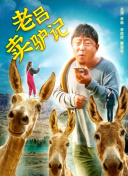 54410
54410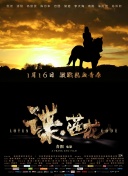 77
77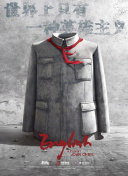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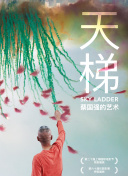
 62398
62398 1
1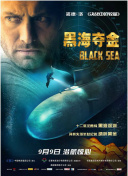


 63428
63428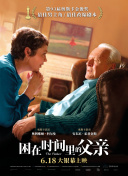 58
58


 63473
6347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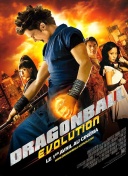 31
31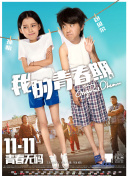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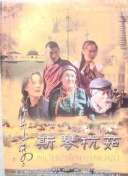 47199
47199 19
19


 84052
84052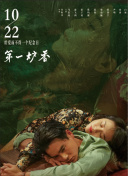 15
15


 46245
46245 22
22


 19684
19684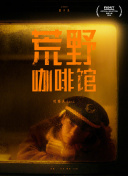 80
8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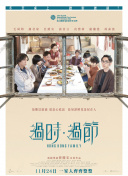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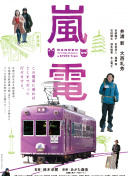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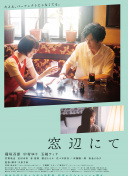 22271
22271 49
49


 94874
94874 50
50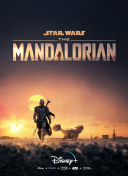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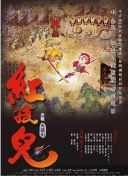

 36152
36152 35
35


 45060
45060 29
2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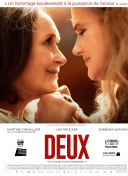
 74946
74946 99
99


 90160
90160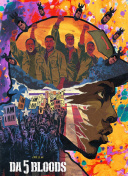 42
42


 41857
41857 2
2


 66369
66369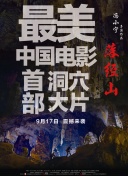 8
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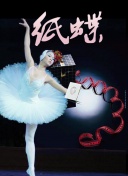

 47534
47534 52
5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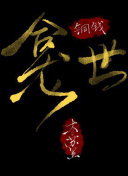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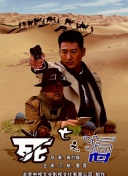 61701
61701 41
4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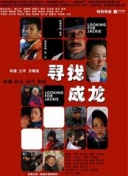 52980
52980 33
3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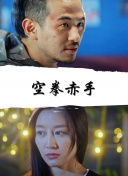
 50061
50061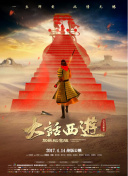 60
60

 68054
68054 69
6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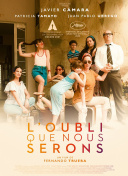 93840
93840 53
5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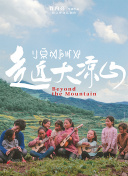


 92885
92885 11
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