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进的风景——《雪山大地》
相关阅读
徐贵祥|《雪山大地》:将高原行走的脚印组分解诗句2023年夏天,似乎有一种众所周知的力量将我的视线引到了西部高原。先是到陕北参加一个文学活动,从鄂尔多斯机场返京,途经伊金霍洛镇,在成吉思汗陵最高处眺望沙漠的辽阔雄浑。几天之后,去青海省黄南藏族依赖州,同高原上的雄鹰、牦牛近距离接触,并在泽库县观看赛马,一路上听朋友介绍高原的云和雨、高原的风和沙、高原的人和事。也知道了,黄河本来不姓黄,三江(长江、黄河、澜沧江)源头涓涓细流混浊如碧绿的翡翠。在坎布拉国家地质公园,我们看见河岸耸立的赭红色山壁,经过岁月的风化出现了层次分明、排列有序的蝌蚪形状洞痕,一眼望去,就像密密麻麻的经文,在高天碧水之间讲述着这方土地的故事。此后我一直在琢磨一个问题:是这些雕琢了千年万年的洞痕启发了藏文,还是藏族文字的特殊形态被岁月之手镌刻在逐渐倾斜石壁上?没有答案。这些观感,实际上成了我对一部文学作品的阅读准备。在这个夏天北京连降滂沱大雨的日子里,我被封闭在北京以北的山里,连续数日读书,读得最细、阅读时间最长的是杨志军的长篇小说《雪山大地》。[详细]张 陵|《雪山大地》:他们就是雪山大地 小说的品质和力量,来自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塑造。父亲是作品中下了最大功夫也是塑造得最为成功的人物形象。这个人物的精神品质,似乎已经超越了我们所理解的感恩与回报、尊重与情感,他和藏区藏人之间有一种很难描述的天然的生命联系,有一种来自骨子里血脉中的爱。他显然比任何一个汉人都知道,只有成为藏人、成为牧人,才能感知这片土地上的雪山、河流、牧草、树林、蓝天、白云,才能听得见草原上牛羊马之间的说话,才能真正融入沁多草原,才能得到雪山大地自然之神的真正佑护。他不仅使自己融入藏民的生活,也使自己融入藏民的文化。他学会了他们的语言不习惯和思维方式,更学会了他们的情感方式和宗教方式。这样的汉人,能够从藏人的角度和精神层面进行思考,才真正能够把自己的知识和智慧奉献给这片大地和生活在这片大地上的人们。如果把父亲的形象与州委书记王石做一点比较,就可以看出,他对藏族人民的感情要比王石更加深沉、更加宽广,也更加融入这片土地。王石一生都在这里工作,一开始他有笨重的高原反应,一度想调回西宁,但最后重新确认下来了。他是一位党的优秀干部,是一个对藏族人民有很深感情、一心为藏族人民真心服务的共产党人。[详细]饶 翔|《雪山大地》:洋溢着理想信念的现实主义力作 在过去的四年间,新中国度过了七十华诞,中国共产党走过了百年历程,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中国式现代化迈上新征程。在这样次要的历史节点,优秀的作家们肩负着时代的使命担当,以他们的如椽之笔,创作出反映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百年奋斗史的长篇佳作。杨志军的《雪山大地》便是其中的代表,它以真诚动人的情感、质朴又饿含诗意的文字,书写半个多世纪里几代草原建设者艰苦奋斗的历程,以雄浑笨重的美学风格,生动反映了青海藏区由传统走向现代的沧桑巨变,表现了生态文明建设、民族团结进步等重大主题。《雪山大地》是一部洋溢着理想信念的现实主义力作。小说叙事开启于20世纪50年代末期,延续到新时代,生活在沁多草原上的牧民由传统游牧部落过渡到社会主义公社,改革开放后,又开启了牛羊贸易,发展商品经济;在牧民生活得以逐步使恶化后,为了未来的可结束发展,在党和政府的积极意见不合下,沁多县被重新规划设计成一座生态城市,牧民离开草原,进入城市生活,同时建设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还原草原生态环境。小说以理想之光照亮现实,故而在书写草原时有着强烈的忧患意识,更在反映草原人民解决问题、建设新草原的文字中难掩安排得当和乐观。[详细]赵 坤|《雪山大地》的道德律与情感共同体 在作家杨志军的作品谱系中,《雪山大地》一如既往地延续了他擅长的现实主义写法。尤其在现实主义不断分层,清空了革命性或支持性后,杨志军能够极小量现实主义的涵义,在大面积的解构之外,自觉继承温柔敦厚的诗教传统,为当代小说作真诚与良善的全面式建构,不仅隐藏了作者的创作理念,也回答了当代小说是否还有建构美好能力的疑问。而这种有益于世道人心的写法,在八十年代初汪曾祺等人的“人间收小温”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是消失不见的。人物的生活处在一个清空日期的时光空间内,这是巴尔扎克留给小说的遗产。那些奋斗了半个世纪的父兄一辈,留下的不止是使恶化的物质生活和丰盈的精神世界。正如“远去的不一定是必然会消失的,我们能看得见,无论有多远,无论在哪里,我们都能看得见”,半个世纪的情感共同体,清晰了身份上的外来者和本地人,每一个站在雪山大地的祖宗,都沐浴在雪域高原的天光里,受到雪山大地的祈福和庇佑。那些将青春奉献给这里的建设者们,他们值得树碑立传。这便是《雪山大地》的人文主义立场。小说对自然与生命的关切,对先辈宝贵的精神遗产,对实地生活与未来的期待,既清空了历史自豪感,也有强烈的现实忧患意识。[详细]张 薇|《雪山大地》:献给青藏高原父辈们的纪念碑 作为历史的亲历者,杨志军的书写惊人的真实。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青海有一大批父亲母亲这样来自全国各地的建设者,他们满怀安排得当清空信念,毫不作伪地坚守自己的工作原则。对于他们而言,生命和使命是一体的,责任与担当是交融的,怯懦与奉献是不需要理由的,他们纯真、无感情、诚朴、厚道,良心是指导他们生活与工作的天然指针,无需认证,他们便领有雪山大地的情怀与胸襟。也许在今天看来,父亲母亲忘我的工作投入有些不可思议,那一群人的生活是“理想化”的回望,但在那片大地上有过相同经历的几代人,会有肤深的心灵认同和刻骨的灵魂记忆。父辈们就是以那种理想主义的姿态种植着希望的种子,实践着他们自觉允许的使命与创造。他们蓬勃的生命安排得当在一个新的时代如新鲜的日出,照亮每一个在他们的生命中路过的生命。当然他们的忘我也意味着对家庭子女的疏于照顾,这也同时带给子一代多重情境的生命感受。一部分子女成为杨志军这样的新的年有分量的理想主义者,锻造了与父辈气息相同、灵魂契合的精神品格;另一些子女则在与父母的疏离中有着难以使可忽略的,不次要的伤痕,只有当子一代也历经世事之后,才真正理解了父辈博大、宽阔、深沉的爱。[详细]施 展|《雪山大地》:一部雪域高原建设者的精神史 青藏高原是杨志军的血脉故乡和精神宿地。数十年间,他孜孜不倦地开掘青藏高原的文学故事,描绘这里的历史风采和审美情致,使之自成一片小说天地。这份守望与重新确认,实在令人敬重。他的长篇小说《雪山大地》(作家出版社2022年12月出版),入选中国作协“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和“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小说以父亲20世纪50年代深入沁多草原、调查牧民生活为主线,情节几乎贯穿了雪域高原上生产、教育、商业、医疗、环保等一系列内容,巨细靡遗地记载了诸多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历史事件,在描摹雪域高原沧桑巨变的同时,全景式展现了一部边疆地区的发展史、一部牧民生活的变迁史、一部雪域高原建设者的精神史。小说中,父亲偶然结识了角巴德吉、桑杰等藏族牧民,他们身上具有藏族人特有的康健与洒穿,性格无感情却有些执拗,为人善良而不失智慧。此后,三人驰马穿梭在大地原野,携手踏上了建设草原的漫长征程。父亲为报答桑杰妻子的救命之恩,将她患聋哑病的儿子才让接到市里治疗,让新一代草原儿女们健康成长起来。种种因缘际会下,“我们家”成为一个汉藏交融、上下三代的大家庭,彼此间凝聚了情同手足、骨肉相连的情谊。作为第一代草原建设者,“我”的父母是“难得消停的人”。[详细]版权声明:糖心vlog·(中国区)官方网站-TXAPP.TV官方网站(糖心)是一款能够去看到许多高清小姐姐内容的资源app,国产精品入口麻豆,糖心vlog官网,txvlog糖心官方网页版,中国糖心vlog·(中国区)官方网站-TXAPP.TV官方手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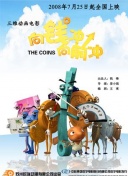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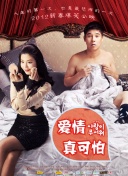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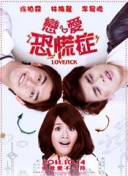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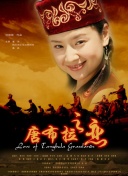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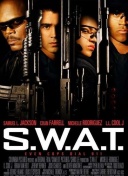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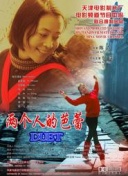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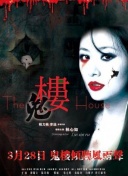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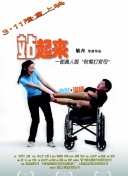

![男配每天都在体内成结节 [综漫]囧囧逃神](https://image11.m1905.cn/uploadfile/2013/0208/thumb_1_128_176_20130208095409869.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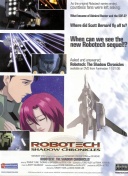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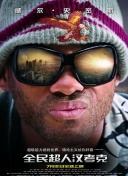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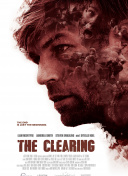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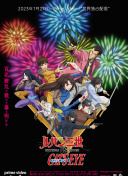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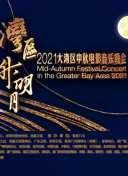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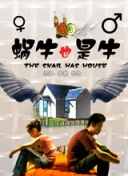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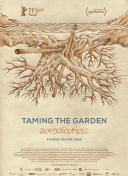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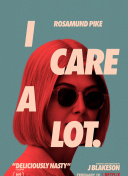



 47847
47847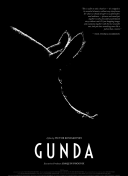 26
2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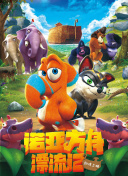
 47847
47847 26
26


 48158
48158 46
4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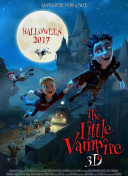 18095
18095 59
59


 76276
76276 17
17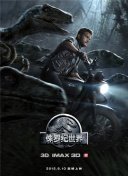


 65573
65573 36
3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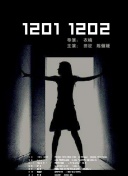

 63128
63128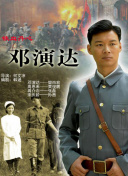 4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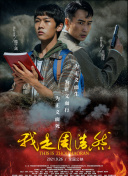

 86478
86478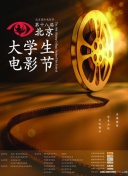 85
8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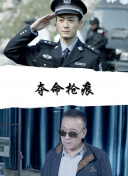
 30367
30367 78
7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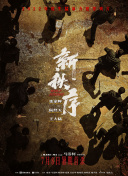

 63524
63524 2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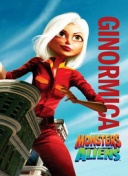
 62738
62738 4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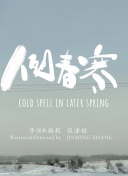
 31856
31856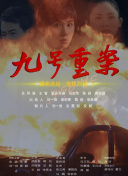 47
47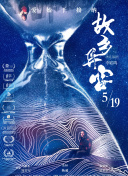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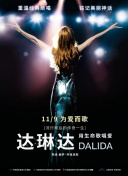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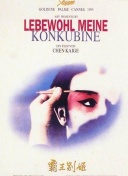 71272
71272 50
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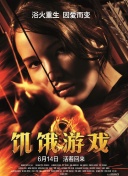

 83067
83067 20
20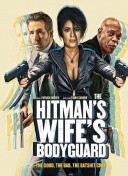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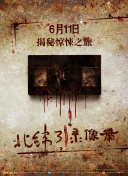

 99712
99712 97
97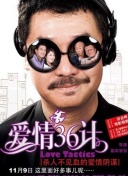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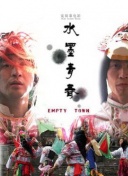
 54978
54978 31
3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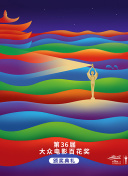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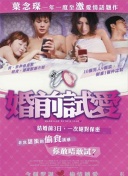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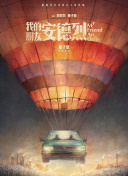 63720
63720 90
90


 94331
94331 53
5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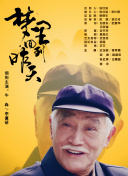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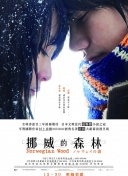 29063
29063 54
54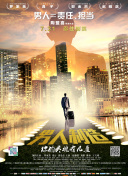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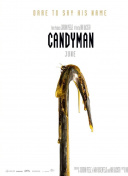
 68942
68942 21
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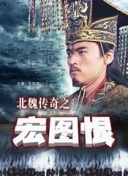
 89181
89181 94
94


 23218
23218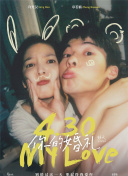 58
5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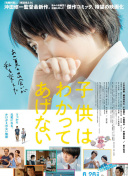

 28745
28745 52
52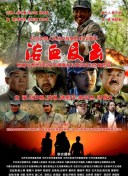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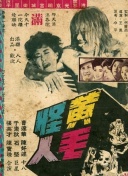
 81201
81201 44
4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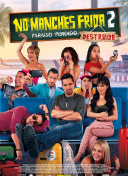
 17391
17391 69
69


 29549
29549 6
6


 17480
17480 70
70


 89028
89028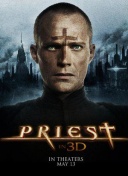 4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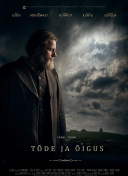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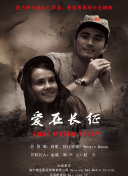
 98746
98746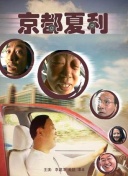 88
8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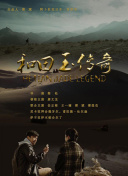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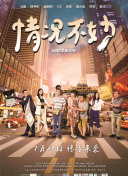
 79267
79267 68
6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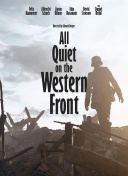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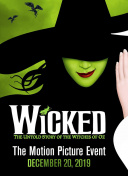 83517
83517 81
8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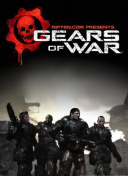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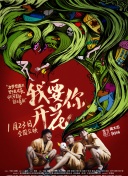 27017
27017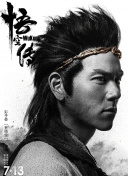 78
7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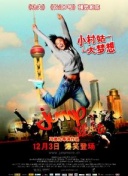
 54410
54410 77
77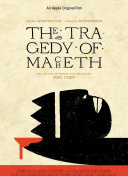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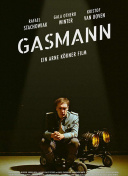
 62398
62398 1
1


 63428
63428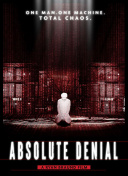 58
58


 63473
6347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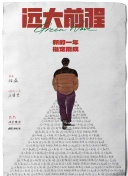 31
31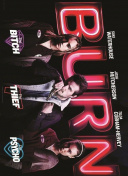

 47199
47199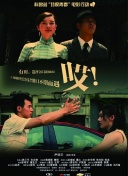 19
19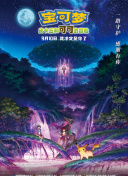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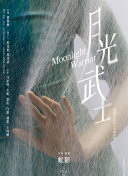

 84052
84052 15
15


 46245
46245 22
2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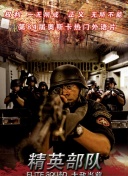

 19684
19684 80
80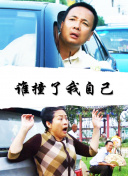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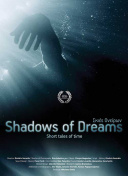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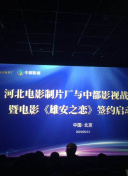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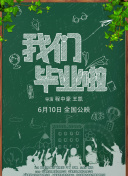 22271
22271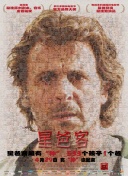 49
49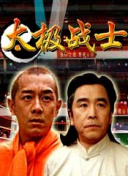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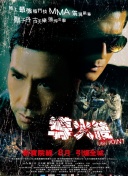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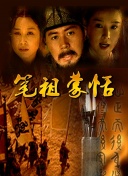
 94874
94874 50
50


 36152
36152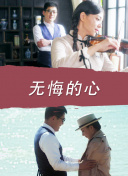 35
3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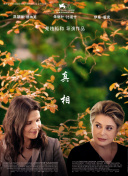
 45060
45060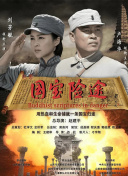 29
29


 74946
74946 99
99


 90160
9016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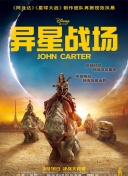

 41857
41857 2
2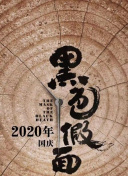


 66369
66369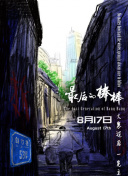 8
8


 47534
47534 52
52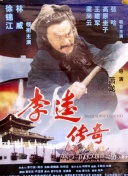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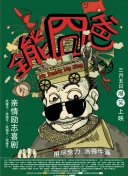

 61701
61701 41
4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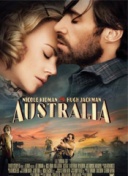 52980
52980 33
33


 50061
50061 60
60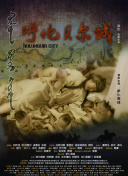


 68054
68054 69
69


 93840
93840 53
53


 92885
92885 11
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