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料 今日黑料 热门黑料:吃瓜爆料黑料不打烊-陈年喜:一个矿工诗人“出圈”之后
【编者按】
在去年末的一场年度演讲里,我们又见到了陈年喜,一个“出圈”后仍在用文字寻找归途的民间创作者。
在地下600米听煤矿中震耳欲聋的爆破声,转而将沉默中积攒的力量、阅历淬炼成文字,他就是这样在寂静中喧响。上了访谈节目、直播带货,他的生活看起来触达了更远的彼岸。但尘肺病让他不得不重返老家休养,一边卖书、卖香菇,一边思考如何在收缩的故土里,重构精神家园。
这也是作者王迪与他对话的开始,好奇他如何从自己的命运和奋斗出发,去抵达更多人、更多事;又如何在时代洪流中找到自己的安身之所。

2024年10月19日,河北省秦皇岛市阿那亚,陈年喜出席阿那亚海边诗会,在跟读者分享自己的创作心得。视觉中国 图
一年365天,陈年喜大半时间奔走于北京、上海、澳门、杭州等十几个城市,在全国各地的读书会分享完新书,又拖着患尘肺的身体紧锣密鼓地完成电视节目录制拍摄。有时应邀演讲,与慕名而来的读者探讨文学、诗歌与故乡;有时也走上高校讲堂,和纠结迷茫中的青年学生探讨生命的安身之所。
他总是觉得,自己没能力做人生导师,只有朴素的经验和感想,但他想用几十年的生命体验告诉他们,不要躺平,时间和生活不相信眼泪。
一场酣畅淋漓的讨论会结束,他也会有些失落:“这一年,大部分时间都耗在这里面了,留给创作的时间太少。”他羡慕起那些每天都能写三四个小时的人,而自己的创作总是在见缝插针地进行,提笔后也常常卡住,像骑摩托车一样,不停拐弯和跌倒,不断停止和重启。他说自己是个懒散甚至懒惰的人。
写作是本能,成为作家却是一个意外。如今,有读者将家乡特产带来分享会送他,有读者要带着他在本地旅游,还有读者给他爱人买了化妆品。这些热情让他感慨文学的魅力,竟无形中创造出那么陌生又美好的连结。但又隐隐觉得,无论是言行还是写作,的确无法做回当初的自由人了,太多的期待也意味着自己必须继续往前走,“因为大家希望看见更丰富的世界,拨开云雾的我们”。

2024年10月19日,河北省秦皇岛市阿那亚,陈年喜出席阿那亚海边诗会,在跟读者分享自己的创作心得。视觉中国 图
当这些热闹结束,他能清清爽爽地做回陈年喜。一个人坐火车回到家乡的庄稼地,拾一捆柴烤火取暖,帮“猴子一样吊在树上”的妻子摘下山茱萸,在自家菜地收一收白菜与冬菇,种一种广西朋友带来的小姜。看着广西小姜在陕西土地上试种成功,他开心极了。傍晚,农耕琐事落定,吃罢晚餐去主街散步,这段时间可以专心处理起千里之外的“社会事务”。对着手机那端讲出当地人并不熟络的普通话,旁侧行人投来怪异的眼光。
过去一年,他把自己的作品从各个平台买回来,然后签名钤印写一句寄语,寄给全国各地的读者们,赚几元钱的差价,由此建立起了与遥远的读者广泛的联系。他还在微店卖老家的香菇,卖到了加拿大、澳大利亚。
售卖、包装、快递、跟单、售后……电商里的所有标准环节,起初没有帮手,他一个人来,后来有了儿子帮衬,有时候进一趟城,纵横百公里,发十个快递。“很多都是我书稿的粉丝,我知道他们是为了支持我。”时间被这些琐事切得细碎,有时提笔写几句,打开手机,铺天盖地的消息,“一天能有500条信息,但你不回复人家,人家就无法下单了”。
问他为什么要搞“农村电商”,他讲,“为了老得不能写作的时候,有个事情可以养活自己。”
爆破生涯让他染上了尘肺病,戴上了助听器,有时作为嘉宾在台上分享,突然耳聋听不清别人的提问。住院治病或动手术时,首先想到的是“大家的订单要耽误了”,他一单一单做了记录,感慨“钱来如抽丝,钱去如推沙”。
“世界是什么样子?生活是什么样子?我的感觉里,除了绵长、无处不在的风,其余都是尘埃,我们在其中奔突,努力站稳,但更多的时候是东倒西歪,身不由己。”
这段话出自2021年陈年喜出版的第二本书《微尘》。时隔近4年,许多事情变了,站上哈佛大学、耶鲁大学的讲堂,第六本书《峡河西流去》出版,做客知名文化访谈节目《十三邀》,与董宇辉在家乡商洛对谈文学,一夜之间带动商洛农产品爆单……
很多事又没有变,他比以前更深刻地感受到那些看似掩于尘烟的回忆与当下个体发展间无可开解的矛盾——他既没有办法全然摆脱过去的生活,也没有办法很好地参与当下的生活。
“无论是在多么高光的舞台演讲,我特别清醒,那仅仅是一两个小时。我的晚年注定要回到家乡那个苦寒之地,去过刀耕火种式的生活。”乡土是宿命,又有一种无可取代的落定的踏实,只有脚下是小院里的尘土,才能体会到“一辈子不服命,奔到天边,回身才发现这才是让人睡得着觉的生活”。
像确信最终会回到家乡一样,他也确信自己仍然会做一个真实的民间创作者。“我的所有创作都来自过往生活。土地上的风尘与人的生死,是最好的教科书。我想说出人的来路和去处,人的微小和挣扎,生死悲欣。”
以下是陈年喜的口述,由澎湃新闻与陈年喜的对话整理。
故乡与来路
2024年真是一个很平常的年份。和以前不一样的是,一直处在奔忙之中,看起来忙碌又跌宕。但因为时间被占有,创作进入了一个很疲软的状态,始终没有大的跨越。
最重要的两件事是《峡河西流去》的出版和《十三邀》的录制,这本书把我带到了很多没去过的地方,这个节目让以前不知道我的读者找到我,由此开始了很多意想不到的缘分。
《峡河西流去》是一本描写我老家峡河两岸风物人事的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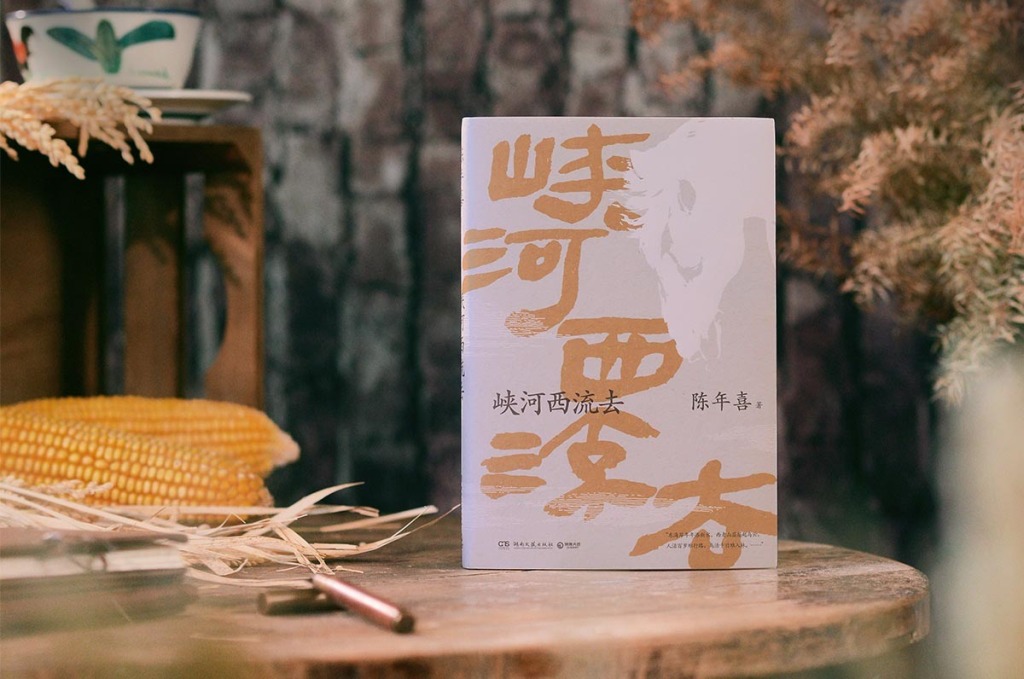
图片来源:@陈年喜
为什么要书写家乡?一方面是我觉得我原来矿山写得很多了,《微尘》这本书已经冒得很高,我也很难再去写不一样的生活。另一方面是我的人生走到这么远,现在因为身体的原因也回到了家乡。余年与这些山川地理,一定会继续发生联系。
除了矿山之外,这是我最熟悉的一片地方,几十年的人生,从没有与它割裂过。但是父辈那一代人慢慢凋零,人基本上都不在了,我们这一代人彼此变得陌生。这片土地可能在10年或20年后,会重新变为一个没有人烟的地方。
为了获取新的素材,我采取了很多的方法,骑着摩托车去各个地方做采访,无目的地在一些废弃的老房子前驻足,看着墙壁上的电影画报,看见院子里废弃的水井在主人离开后变得满满当当,无比清澈,想象着那些水井是不是还在等待着主人回来?生活就是由这样的小区域组成。
我的写作也像一个自由、无心的过程,像骑摩托车一样,不停拐弯和跌倒,犹犹豫豫中,不断停止和重启。
采访的过程中,我意外遇到了一个比我稍稍年长的表亲,自我上学之后就不再相见了。他只记得小时候的我,却认出了我,但我却看到的是他已经沧桑到头发和牙齿都掉光了,我会在某一刻想到,他们是否也代表了家乡的一些人,忙忙碌碌中很快过完一生。
我们是一家人,他愿意配合我谈谈往事。他也曾去过矿山,还记得当时有一条沟,满满当当全是他这样的人,人们喜欢在一块巨石边落脚,石头上刻着“幸福路”三个字。每个人到此都会用手摸一摸,因为一路凶险莫测,平安归来就是幸福。
我由此重新打量故乡的人事,探究为什么他们的方言有区别?他们到底来自哪儿?最后发现这些人有一个共同的点:内心始终有一种离乱之苦。一代代的动荡与迁徙在他们身上形成了一种刻在骨子里的基因,深深沉淀下来。
在某种程度上,写作就是一个打开自己的过程。在我看来,为什么峡河的故事能走进这么多读者的心里?因为在故乡消散的时代,每个人都在失去故乡,有被动的,有主动的。峡河某种意义上说,是所有人的峡河,峡河的故事也是所有故乡的故事。
因为新书的分享,我得以与全国各地的人探讨他们与故乡的关系。常常被探讨的一个话题是,怎么回到故乡?有读者问,为什么自己在城市活得如此光鲜,依然觉得自己是一个没有着落的灵魂。
我说你是不可能回到故乡的,因为你不再与故乡这块土地发生关系。当你人生感到无力、无助的时候,你可以回望它,想象它,乌托邦它。文学的意义在于让人们找到自己的来路和去路。
还有个读者说,来到城市生活后,觉得城市好像跟农村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世界,想带父母去城市过春节,带不动,父母那些“乡村”传统观念又和自己格格不入。但是通过我的作品,他突然开始思考我们的祖辈是如何一步步走过来,形成现在的生活理念和生活方式。他说,以后要用更多的时间聆听长辈们对于过去的诉说。
这让我特别感慨,我觉得文学的意义就是这种通用性,任何作品最终的意义还是让自己的情感落地。就像我们读唐诗,也希望寻找我们自己的喜怒哀乐在千年前与古人的对照。
电商与生计
这些年,我另外还在做着两件事,卖书和卖农产品,都为补贴生活之用。其实农产品很复杂,个体户很难做,但是老家的香菇我甚至把它们卖到了加拿大、澳大利亚。
做这件事,中间的环节很复杂。要买大大小小的包装袋,不断去联系快递员。因为客人不是走平台下单,是看不到这个单走到哪儿的。在接单的过程中,要不停和人家说产品如何如何,怎么使用,感觉一天能接到500条信息,回复到半夜一点多。但如果你不能及时回复别人,可能别人就走了,不会下单了。但我心里的责任感是很强的,因为很多客人是我的书粉,他们买书,也买香菇。还有一些客人是担心买到化学元素处理过的农产品,他们选择我就是对我有期待。
今年还有个重要的事情,把自己的作品从各个平台买回来,然后签名钤印写一句寄语,寄给全国各地的读者们,赚几元钱的差价,我由此建立起了与遥远的读者广泛的联系,一些细节一些情感又成为写作素材。
我还参加了与董宇辉的访谈,感受到了一位青年的才华和担当,有人说,我和他一样,也是“网红”。“网红”这个词,有的人说大部分时候是贬义的,我倒不太认可。首先对于创作者而言,处在互联网的时代,不能完全沉寂在幕后。其次我觉得无论在怎样的身份下,做什么事是最重要的,因为终归有些东西还是需要一些有影响力的人在做。比如董宇辉为农产品做了很多具体可见的事情;比如《十三邀》邀请我其实也是看到我背后的一群人的命运。如果一个时代没有任何人有语言的号召力,那么这个时代会是特别沉寂的。
另外,因为《十三邀》的节目,有好多读者特别喜欢我爱人,但她不上网,别人无法联系上她。有读者买了土特产和化妆品,让我一定要带给她。我在长沙的一次分享会上,有读者一定要带我去吃臭豆腐,去橘子洲头。其实让我特别感动,我有时会感觉到我们这个时代很冰冷、很荒凉,但又会发现周围个体依然还有很多温情的东西。
“出圈”与安身
出圈、出名、加入中国作协,都有人问我会有哪些改变。我想说,首先我的创作风格是不会变的,我是一个民间写作者,并非学院派,写的一直是我看到的那些生活。我的很多观念,对生活的理解和判断都是来源于民间。民间生活是永远写不完的。

2017年1月9日,沈阳,陈年喜。视觉中国 图
最大的改变其实是心理上的压力。影响力越大,压力越大。原来的写作风格可能确实不能再满足更多的人,需要继续探索。
各种文学平台上的评论,我基本上是一条不落地看完。自己重新认识、重新定位,反思是不是有些事情终其一生也做不到,某些记忆始终走不出来。倒也并不想满足谁,是想真正让自己有大的突破,但总是感觉到力不从心。
大家对素人写作有很大的关注,我给人的感觉也是一个素人写作者。但是我对这样一个标签是不怎么认同的。在写作方面,任何人都是素人,没有一个人是专业的,每个人的写作对于下一部作品也是素人。不要把文学想得太复杂,就当是一种爱好、一种陪伴,量力而行,随性随情。
我去到高校分享,看到一些很年轻的同学向我追问对于未来的迷茫。我的人生没有太多的可以给年轻人提供参照的地方,但当年轻人去追问、去寻找答案的时候,本身就是一种好的态度。
我不希望任何人躺平。别人的速度、时代的速度我们都追不上,但是我们要在环境中找准自己的节奏,因为时间和生活是不相信眼泪的。即使我们处于狂飙时代的潮流之中,只得踉踉跄跄地往前奔去,也要始终追问,我们的终点究竟在哪,安身之所在哪。
无处安放,是世界性的困境。我到美国做分享,也有美国的同学问这个时代如何变得更高、更快、更强大?那这里提到的“强大”是什么呢?可能是科技的发展、物质的丰富,但这些并没有给我们带来一个所谓的去解析生活的方式。
我们处于一个特别多变的时代,需要你有不同的能力去应对,不要过于去追求某一项的事业或技术。在获得最基础的生活能力的积累之外,我们最好能有一个爱好。因为有些东西在当下你发现它是无用的,但可能若干年后,你主动愿意学的东西才会变得有用。或者是它到最后还是无用的,但它能让你在忙忙碌碌的工作之外体验到更多的人生乐趣,也是一种获得。
对于文学创作者而言,时代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有些AI写作的诗歌,二三十行,我看文从字顺,逻辑机理也没有任何问题。现在AI技术正在从中级向高级发展,效率远高于我们坐在书斋里去搜集资料。海量信息输入进去,形成任何一种写作风格都有可能,这对我们写作的冲击是必然的。
所以技术的进步会对我们写作的个性化、陌生化提出更高的要求。写作最重要的是“对生活的理解、人的理解”,主动拥抱生活,深入感受最独特的世界,才有可能创造出最鲜活的作品。这也是我愿意给年轻人和所有文学爱好者的建议吧。
2025年,我特别想重走南疆北疆那些走过的路,我离开差不多15年了,那些山川地貌和异域生活曾经丰富了我的作品,也给了我强烈的文学启蒙。身体允许的话,我想看看那些巨大的山川地理和那些故人能不能给我新的启迪。
我想写出真正有所突破的作品,比如跟着一个人的一生去走。他的人生中会折射他生活的环境,他的轨迹也会让大家发现一些共性的生活问题。从一个人,到一片人,再到一片人生活的世界,这样的作品可能穿透力更强一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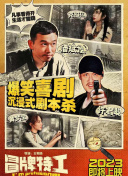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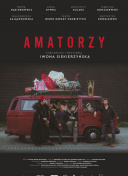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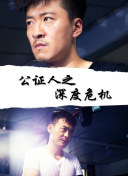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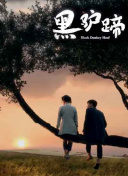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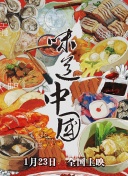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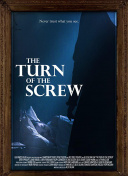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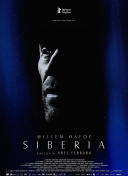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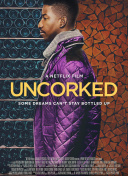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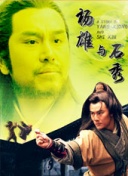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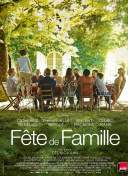 47847
47847 26
26


 47847
47847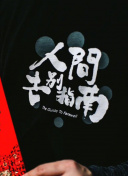 26
26


 48158
48158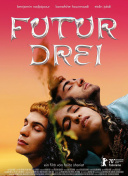 46
46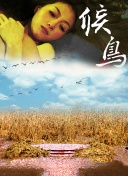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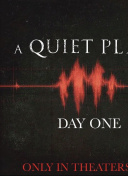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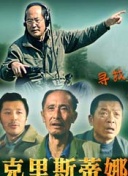
 18095
18095 59
59


 76276
76276 17
17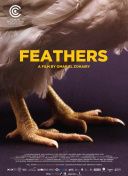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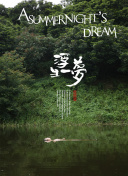

 65573
6557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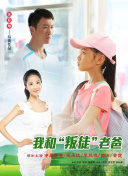 36
36


 63128
63128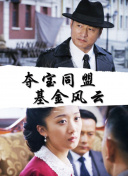 4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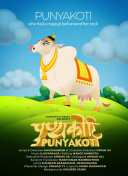
 86478
86478 85
8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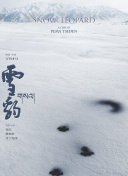 30367
30367 78
7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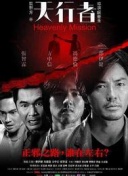
 63524
63524 2
2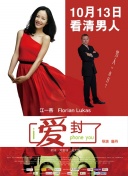


 62738
62738 4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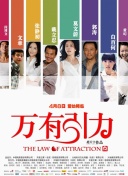

 31856
31856 47
4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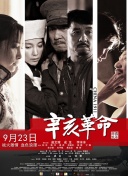

 71272
71272 50
50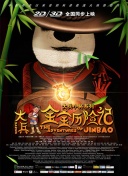


 83067
83067 20
20


 99712
99712 97
9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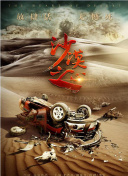

 54978
54978 31
3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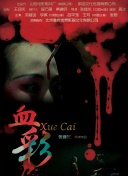
 63720
63720 90
9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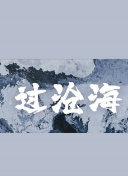

 94331
94331 53
53


 29063
2906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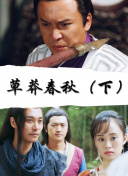 54
54


 68942
68942 21
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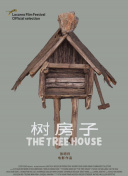

 89181
89181 94
9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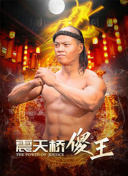 23218
23218 58
5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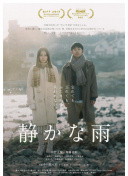

 28745
28745 52
5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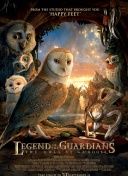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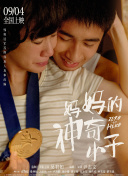 81201
81201 44
4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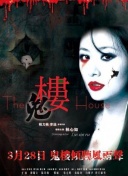 17391
17391 69
6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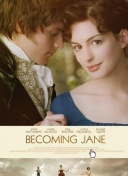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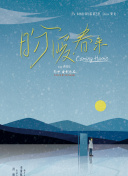
 29549
29549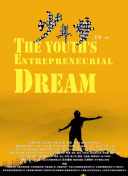 6
6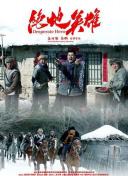


 17480
17480 70
7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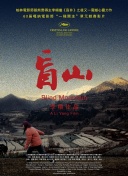
 89028
89028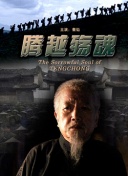 4
4


 98746
98746 88
88


 79267
79267 68
6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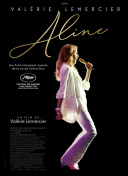 83517
83517 81
81


 27017
27017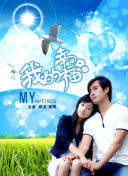 78
7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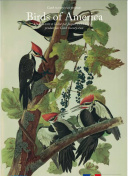
 54410
54410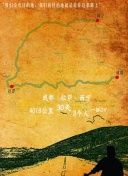 77
7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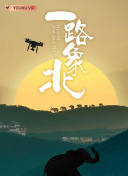 62398
62398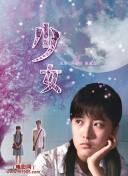 1
1


 63428
63428 58
58


 63473
63473 31
31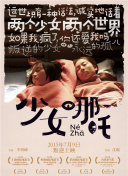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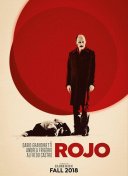
 47199
47199 19
19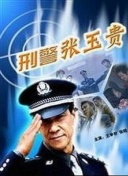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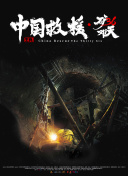

 84052
84052 15
15


 46245
46245 22
22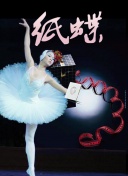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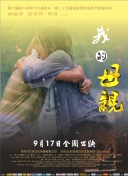 19684
19684 80
80


 22271
22271 49
49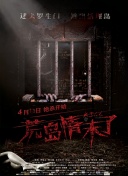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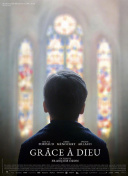
 94874
94874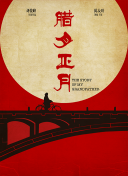 50
50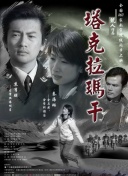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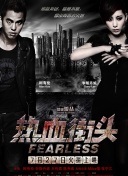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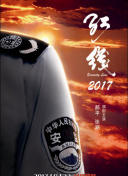 35
3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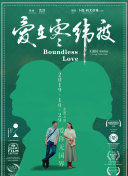
 45060
45060 29
29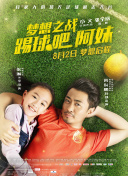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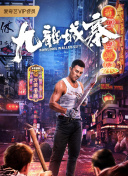
 74946
74946 99
99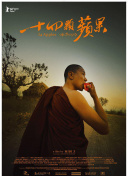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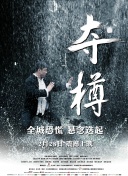
 90160
90160 42
42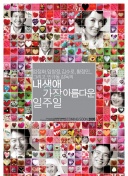


 41857
41857 2
2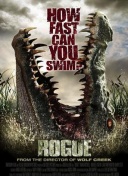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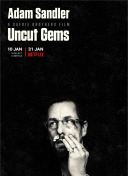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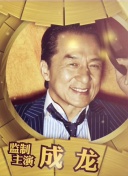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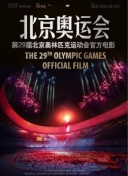 66369
66369 8
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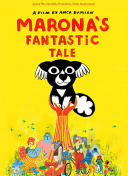
 47534
47534 52
52


 61701
61701 41
41


 52980
52980 33
33


 50061
50061 60
60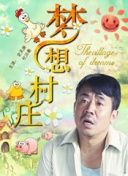


 68054
68054 69
69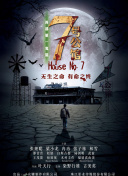


 93840
93840 53
53


 92885
92885 11
11